
【ps:近期如出现邮箱无法发送可戳微博@前任A小姐 私信】
竹之花
作者:叶月言
我和一个男人相爱了。
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明明比任何人都清楚,却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
稗田家的女人,没有与人长相厮守的自由。
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做呢?
要怎样才能完成对那个人的承诺呢?
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只是,每当想起这份恋情,心底就会涌出一股刺鼻的悲哀之情。
稗田阿求(序)
老人鞠偻着身体,在那棵秃头老树底下坐了好几个钟头。他抖了抖手中的烟杆,这才发现烟草已经被飘落的细雪给浇灭了。不过老人只是将杆头的积雪拂去,没有在意火焰熄灭的事。于是,被浇灭烟草的火星的灵魂,化为一缕青烟轻抚过老人的侧脸后,便朝着细雪纷飞的苍穹飘然远去。老人仍旧静默地坐着,似乎丝毫没有发现一旁升起的青烟。
老人的脸看上去饱经劳动和风霜,有一种属于农民的精悍。肌肉紧致,皱纹也像被攥紧着的毛毯似的拧在一块。可以想象,他年轻的时候是多么强壮的一名青年。然而,他的眼睛却成心要跟这张精悍的脸唱反调,显露出一种缺乏生命力的疲惫。
远处传来咚咚的响声,是一群小孩子在打雪仗。大冬天的,那些孩子们却都穿着单衣,有些还是赤脚,真为他们的身体捏一把汗。话虽如此,但这也只是大人们的看法。孩子们对自己的身体全然不顾,个个都喜欢往雪深的地方跑。抓一把蓬松的雪块,团成紧密的雪球,再朝另一个小孩的脑袋上一扔,最后还要盯着对方的狼狈样哈哈大笑。
男孩子喜欢打雪仗,女孩子们就聚在一起唱歌。民歌没人谱曲,因此每个人唱出来都不太一样,大家一起唱,就显得有些怪声怪调。那是一首讲竹子的民歌,这里的小孩都是从小唱到大,可老人不会。因为他原本并不是这儿的人。老人一生中曾数次听到这首歌,但到现在都还记不得歌词。几个青年人扛着长杆菜蒌往附近的小路经过,对他喊了一声“老大好!今天也在这儿休息呢。”说完便离开了。他点点头,算作回应。但他的身体依旧鞠偻,依旧以失神落魄的表情注视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注视的前方。
当此之时,树梢上一块初融的积雪,被孩子们震天的喊声击落,啪嗒一声涂在了他已近花白的头顶上,而随着雪块落下的,还有一双少女的芊芊细手。那双手攥着一套貂皮披风,顺滑的貂毛在老人肩上随着寒风起伏。
“终于……终于找到你了。”
少女说道。
这是一个体型娇小的少女。身着的加厚和服是最小号的,但在她身上还是显得有些宽大。粟色的短发只有齐肩高,头顶上扎了一朵雪白的山茶。
老人没有回应少女的搭话。于是少女继续说。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个人默默支撑着这个家……”
“……”
“你就这么讨厌这个家……这么讨厌我吗?我……”
老人还是沉默,少女开始激动起来。
“……为什么啊!你倒是说句话啊!”
这是近似于哭泣的质问。和服衣袖被少女攥的很紧。
然而,与少女形成鲜明对比的老人,一如既往地将烟斗上的积雪拂下,仿佛身心都降到了和这冬天同一温度。
“你莫非觉得我的日子过得很苦?怎么会……”
老人的话像是从喉咙中挤出来的,但并没有勉强的感觉。干涩的声音或许只是太久没开口的缘故。
“嘿……嘿咻。”
他护着因老迈而脆弱的腰杆,慢慢从地面站起来。
“哎呀,脚都麻了,溜达两圈吧……”
说着,就要向前踏步。
“要不要,跟我去那里看看?”
“……”
语毕,老人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那刚要渐远的背脊,再一次被少女追上。
而直到这时,老人都还没有正眼看过少女。
老人把少女带到了一片墓园,两人在路上都是默默无语,唯有积雪被踩扁的咯吱声响彻耳畔。
冬天的墓园比平常更加寂寥,生命力顽强的野草也已近乎荒芜。寒冬将墓园变成了真正的无生之地。偶尔会有几只乌鸦嗄嗄地叫着,从远处秃树枝头掠过,但那听起来更像是死者的哀嚎。
“这里是……”
少女跟在老人身后,停在了两座墓碑前。
老人俯下身去,拂去了碑上的积雪。墓碑的铭文写道“稗田家先祖之墓”。
“这里,长眠着两个女人。”
老人开口,声音不像起初那般干枯了。
“一个是我爱的女人,另一个,是爱我的女人……”
“对不起……让你苦等了……”
少女的声音好像是有了什么觉悟。
“我一定会把所欠的还给你……”
“不,不用……”
老人再一次挺起腰杆,从墓碑旁站起来。
“这不是你的错。”
“但是……”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还不知道……”
老人的话没有说完。
“不,我知道。我全部都知道,所以我才要还给你,所以我才要……”
少女没有再说下去。她那娇小的身影被寒风吹得十分悲凉。
老人继续说。
“那么,今天就讲一讲好了……在她们面前。”
“讲什么?”
“我的过去。”
老人吸了一口已经熄灭的烟斗。少女注视着他的背影,仿佛他过往的人生正化作青烟从头顶上升起。
稗田阿七
无论怎么想,那也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
稗田家是镇子上的名门望族,他们家世世代代记录着幻想乡的历史。不过奇怪的是,家大业大的稗田,却从来不请长工,只在过年或者农忙时期雇一些短工帮忙。于是,在这很久以前的往事当中,老人还未成为如今的老人。那时候的他,正作为稗田家的短工,随父亲到镇子上来挣钱。
稗田家的小姐和随父来打短工的少年年龄相仿,加上稗田家是独女,来打短工的人中,带着孩子的也只有少年的父亲一人,因此,小姐和少年,在刚见面的时候就有相互亲近的意思,农忙时少年努力干着农活;过节时少年操持家务,这三来二去之后,两人已可以说是十分熟稔了。
“呐,你看,这里风景很好吧?”
稗田家的小姐身着一身缀花和服,踩着木屐攀上了树梢。
小姐的话是对少年说的。而此时,那被询问的少年正丢下农具,跟在小姐后面。
“小心点啊阿七,你那身衣服不适合爬树。”
少年如此叮嘱,但阿七却不予理会,仍旧自顾自地开口。
“站在高处,可以看到远处那片竹林噢!”
少年从阿七的肩旁探出头去,顺着阿七所指的方向,果然有一片大大的竹林。因为相隔太远,本来面积广阔的竹林,在初春朝阳的映照下更像一湾翠绿色的湖泊。少年本来该对这片竹林十分熟悉,毕竟经常跟着大人入林伐竹,不过,在近处片面地体会竹的苍翠,与在远处观赏竹林的群体姿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因此,原本三天两头就要去一次的竹林,此时在少年眼中却变成了一个新奇的地方——一片翠色欲滴的湖泊,让人看了就想在其中徜徉。于是少年发出感叹“真的啊!竟然能看到那片竹林的全貌!”
“嘿嘿,我没骗你吧?这里可是我的秘密基地。”
阿七对少年露出了自豪的笑容,下一秒又向更高的方向攀去。与那身端庄的和服不同,阿七本质上是个活泼的女孩。只是出生在稗田家,从小就接受了高端的礼仪教育,因此不可避免地,阿七的身上兼有端庄和活泼两种性质。平时在镇子上,为了不辱稗田家的地位,她一直保持第一种气质。这对阿七来说并非难事,但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于是,在家臣们忙里忙外,没时间看她的时候,她就偷偷从镇子里溜出来,溜到山头上这棵年已近百的老树下休憩玩耍。这时的阿七,毋宁多说,已完全从一位注重礼仪教养的大小姐变成了活泼的丫头。
老树的树干壮硕,树梢离地面足足有两间房的距离,每值酷暑难耐的夏日,阿七便会坐在树梢上摆荡着双腿,倚靠着巨大的树干朝远处张望。凉爽的山风从遥远的东方破空而来,拂过阿七的背脊,又将叶间碎影摇得沙沙作响。而阿七的眼底,长势正盛的春麦田连成一片金黄色的汪洋。山风越过老树,朝汪洋当中投身而去,于是春麦们无一例外地摆动起身躯,金色的麦浪起伏,一直荡漾到汪洋的尽头。
知道树梢上绝美风景之人,如今,除了阿七之外,还多了一名少年。
这是两人之间的秘密。
“阿七,别爬太快了,小心掉下来。”
“才不会呢,我已经爬这树好多年了。”
话音刚落,阿七踩在树纹上的木屐猛然脱落,本人也无法保持平衡,从少年头上跌落下来。
“哇啊啊啊——”
“唉,我就说嘛。”
木屐最终落到了地上,但阿七却被少年稳稳地接在了怀里。
“谢……谢谢。”
阿七的脸有些泛红。
“所以刚刚就说叫你别爬那么快了嘛。”
少年把阿七放了下来。
“抱歉啊,让你担心了。”
“没事,下次注意一下就好了。就算你说在这树上玩了很多年什么的……你不是才十二岁吗?”
“对啊,但是,你也是十二岁啊。”
“我的事情怎样都好啦。年龄小不说,还穿木屐爬树,这也太没常识了吧。”
“可是,赤脚的话,走在树梢上会很疼的。还有,你说话真像大人们,小心以后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噢。”
阿七辩解似的说道。
“就算我以后变成老头子,你还不是得由我来救。知道这个地方的只有你和我,不是吗?”
“对啊。”
阿七对着少年展露了笑容,仿佛在强调这个两人共有的秘密。山风缭乱了阿七尚未绑紧的头发,左眼眼角那颗可人的泪痣,正随着头发的浮动若隐若现。
“到时候就麻烦你啦。”
阿七的头发和平常人不同,是白色的。
闻言,少年似乎感到无可奈何一般挠了挠头。
“唉,我家这个东家可真是……”
“嘿嘿,过来吧,我们到这儿来看。”
阿七拉起少年的手,走到了树梢边。
“这里视野很好吧?能看到你们经常去的那片竹林。”
“的确,比我想象得要漂亮。甚至比路上的花好看得多,明明只是竹子。”
听到这话,阿七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搞得少年有些不好意思。
“怎……怎么了?为什么要笑啊?”
“没什么噢,只是觉得很有趣而已。”
“这……”
“呐,你知道吗?竹子也会开花。”
“诶,是吗?”
“嗯,虽然很少见,但的确会开花的。是一种白色的小花,很漂亮。”
“白色的啊……真想看看。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呢?”
“……竹子将死的时候。”
“啊……”
“竹子开花是凶兆。开花不久,竹子就会死掉的。这个镇上有首歌就是唱这个的,你没听过吗?”
少年挠了挠头。
“或许听过吧,不过整天都很忙,就算听到其他人唱也忘了。”
“那,我唱给你听吧?”
阿七如此提议,并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可以吗?”
“当然。这是住在这个镇子的人,都必须知道的一件事。”
语毕,阿七清了清嗓子,开始唱起歌来。她的声音很清脆,像鸟一样。她开口歌唱的时候,鸣蝉、树叶、山风都停止了声响,仿佛世间万物都因为她的歌声而沉寂。或者说,万物的声音被她清洌的歌喉给掩盖了。由小到大,由低至高,这首咏竹之将死的歌曲,从她的唇齿间如清泉般流泻而出。
那歌中唱道:
竹之花,
人言其身。
在华彩初放之时,
便已凋落成泥。
……
少年注视着高歌着的少女的侧脸。少女遮住右眼的刘海被山风撩起,双眼微闭,目光中滴落下一丝与刚刚的气氛丝毫不符的悲情,左眼下的泪痣越加显眼起来,而留得稍长的侧发则在半空中飘散,偶尔拂过少年的面颊,使其泛起一丝痒意。
眼前的光景太过梦幻,简直不像是现实中能见到的。
少年看得呆了。甚至待到少女唱完之后都还没回过神来。
这是少年第一次完整地听到这首歌,而下一次听,已经是十年后的事了。
少女抿紧嘴唇,注视着少年。那脸色中有种说不清楚的悲哀,仿佛她只要一放松对表情的控制,就会哭出来似的。
“开了花,就只有死路一条……”
“……”
“稗田家的女人,也是如此。”
少女如此说道。
名为稗田阿七的少女,在十二岁那年,对少年如此说道。
然而,对于少女的话,当时的少年并不十分理解。他只感受到风的流向似乎比刚刚还乱了一些。少女紧绷的双颊犹如冰冻的河面,而颤抖的嘴唇后面则汹涌地交织起多股暗流。当少年确切地察觉到少女身体里暗流正无可避免地冲向毁灭之时,已经是几年后的事了。
一滴带着咸味的水珠从斗笠的阴影下划过,他觉得胸口变得更加粘稠了。衣服被汗水浸湿而紧贴在身上,好像已经变成了皮肤的一部分。微风从镇子的方向迎面而来,带着咸湿的味道和体液蒸发的微凉。他放下伐木斧,用空闲的手扶起遮阳斗笠,正待往西方仰望之时,不知何处的耕牛发出一声长啸。于是,这位手扶斗笠的青年的目光,便随着悠长的牛吟声直向落日山头袅袅而去。
自十二岁的事情之后,已经过了五年。当时跟着父亲忙里忙外的少年,已成长为了一名独当一面的青年。他已经和一棵小树同高。他的肌肉因劳动而紧致,皮肤呈健康的古铜色,声音变得沉稳,而那张尚未退却少年独有的活泼的脸颊,则多增了几分成年人的坚毅。
正当少年仰望夕阳之时,不远的前方传来一声和耕牛一样低沉的催促声。
“小子们,赶快走,要赶在祭典开始之前回到东家,咱们的事情还多着呢。”
说话的人似乎已经年近五十,但身体仍然精壮。他是稗田家每年所请的短工中年龄最长,工龄最长的一个,因此,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其他工人都认他作头子。青年也不例外。
听到这声催促,仰望着夕阳的青年,以及身后其他身着白布衣、肩扛木柴竹竿的短工们,都在无言当中加快了步子。
一年一度的祈福祭典,今年也如约而至。青年作为稗田家的短工,当然要帮忙。
短工队伍很快就回到了小镇。当青年扛着一捆干柴拐过稗田家门外的转角处时,铁匠铺的小女儿良子,正手托一碗天妇罗与他擦身而过。还没待他反应过来,良子的哥哥三郎已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面前,并穿过他扛着的木柴,朝良子飞奔而去。
无需多言,镇上已是一片热闹非凡。作为小镇大户的稗田家,此时也为了祭典的准备而忙得捉襟见肘。然而,除了为祭典忙碌之外,稗田家的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亟待解决。
“小姐――小姐她又不见了!”
喊话的人是稗田家中的女仆,她一边大声叫着,一边跑到刚进门的短工队伍旁边。
“镇子里都找遍了,但都没有小姐的影子。”
这话是对着短工头子说的。于是他脸上露出了不愉快的表情。
“明明都要到祭典了,东家还真能给人添麻烦。”
话虽如此,但短工头子并没有紧张的感觉。他转过头看向青年。
“东家又不见了,去找找吧。”
“哦,好。”
于是,青年冲出大门,心中想道“是不是又到那里去了呢?”
所谓的那里,便是只有青年和小姐两人知道的“秘密基地”。
青年越过山头,来到了那棵年龄过百的老树下。稀疏的树影在青年脸上不住地荡漾,他朝树梢间呼喊。
“喂,大家都在找你呢。”
随后,仿佛是要回应青年的声音一般,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攀着树枝在树叶深处出现。这便是稗田阿七。
阿七蹲在树梢上,两手左右抓握起两边的树枝以保持平衡,接着,对着树下的青年报以微笑。
经过五年的时光,阿七的改变或许比青年更大。长了一头这点自不必说,比这更加惹眼的是,阿七第二性征的发育之后,已经从幼时的身体完全变为了女性的身体。
或许是因为锦衣玉食的缘故,阿七比以前要胖了一些,但无论是身上还是脸上都没有赘肉,莫如说,在那一身缀花和服的映衬下,阿七显出一种大和抚子与纯情少女之美相融合的气质,并且,这是将两者最美的特点进行融合的一种气质。
第二个能够表现阿七淑女变化的地方,是脸庞。不知为何,随着年龄增长,她的皮肤变得比以前还要白皙。但这种白皙,除了包含女子特有的细嫩之外,在阿七身上表现出的,还有另一种背离健康一词的疾病感。一言蔽之,就是“病态的白”。是那种无法想像自然界中竟然天然存在的皮肤之白。而这种白皙,与她根植于贵族教育当中的优雅气质相配合,可谓是“病美人”的象征。
这样的阿七,对树下呼唤着自己的少年报以的微笑中,无疑是带有一丝预料当中的喜悦之感的。然而,明明是意料之中,她却还是刻意摆出一副捉迷藏被抓到后的模样。
“被你找到了呀,真是的。”
青年也对她回以笑容,只不过这里面更多的是赧羞之意。因为他从她的眼神中,体会到了一种活力之光,而这股活力,又恰恰与皮肤间病态的白色形成对比。仿佛烈焰与寒冰,在不断融合与分离中孕育着新生和死亡。青年便是体会到这种伟大而又异常的美丽,才在惊叹之余,除了微笑无法做出其他反应。
阿七扶着树枝站了起来。
“能不能在下面帮我看着点,我这就下来。”
“啊……嗯,好。不过……”
“别担心,这点高度不算什么的。”
阿七说着,再一次从树梢上遥望远方。这是能看到小镇全貌的巨树之顶。自己,还能再看到几次这样的景象呢?
她不再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树下还有一名青年在等她。
“我把鞋踢下去了哦?”
“诶……诶?”
“我也要下来了,好好接住哦?”
没有理会青年在慌乱之中发出的“慢着!慢着!”的阻止声,在青年刚刚接住自己木屐的同时,阿七已纵身一跃,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了青年。
“嘿咻!”
也不知是谁发出的叹声,但就结果来说,阿七还是被青年稳稳地接在了怀里。
“麻烦你咯?”
“没……没事。”
“呵呵呵,你刚刚摸我屁股了吧?”
“才没有!”
对于自己的玩笑正经地否定着的青年,阿七感到十分愉悦。而与之相对的,是少年绯红的双颊。她喜欢看到他惊慌失措的样子,于是,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左眼的泪痣在肌肉的颤抖下稍稍形变,透露出一种妖艳之美。
“怎么?抱上瘾了吗?”
阿七又戏谑地顶了青年一句,青年这才回过神来,一面“不是,不是”地叫着,一面将阿七放了下来。
“我有些累了,我们先在树下休息一会再回去吧。”
虽然工头那边催得急,但原地休息毕竟是东家的命令,自己没有立场拒绝。
于是青年和阿七,就像童年时期的二人一般,一面感受着微风轻抚,一边靠在粗大的树干旁休憩。
“你说,我们有多久没这样一起玩了?”
阿七突然问道。
“谁知道呢……大概也有几个月了吧?最近家里的活挺多的,今晚又是祭典……”
“是啊,所以最近我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爬树,一个人下来,真寂寞呢。”
“喂喂,别一个人做爬树这种危险的事情啊……要是摔下来怎么办?”
闻言,阿七又笑了起来。
“怎么?担心了?”
青年愣了一秒,随即说道。
“我……当然担心啊,毕竟你是东家嘛。”
“那就是说,如果我不是东家,你就不担心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呵呵呵。”
“别,别笑啊。”
“呵呵呵。”
“喂……”
“好啦,不笑啦。”
少年没有说话,但绯红的脸稍稍平静一些了。
“呐,你以前不是说过吗?”
“什么?”
“就算我从树上落下来,你也会接住我的。”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还有,以后会买一大片田地,然后娶我当媳妇。”
“这……可能需要你再等几年。”
青年确实曾立下过这样的承诺,然而,过后几天,就被工头警告说“要看清自己的地位,别对东家动脑筋”,那之后,青年就从未说过这种话了。但这并不代表他已经放弃,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更加努力。少说话,多做事。
“恐怕,我以后再想像这样爬树,也没机会了。”
阿七突然这么说道。脸上开始露出悲哀之色,这是和幼时充满活力的笑容截然相反的,一种仿佛意识到人生无常般的表情。她总是这样,在转眼之间就变得哀伤起来。仿佛对她来说,滋生快乐之感比表现悲哀之情更加耗费体力。
青年问道。
“怎么突然这么说?”
“这副身体,已经不行了。”
“喂,别说不吉利的话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阿七说,脸上的笑容已经完全退却了。
“我呢,其实并不怕死。”
“我啊……只是为了记录幻想乡的历史,才出生在这世上。
就算死掉,记忆也会原封不动地传承下去。
对我来说,所谓转生,不过是丢弃老去的身体罢了。”
青年听了,若有所思地遥望着远方,但并没有露出阿七意料当中的惊慌表情。
半晌,青年开口。
“我虽然不懂什么转生之类的,但是,你现在不是还活着吗?”
说着,转头凝视起阿七的眸子,阿七也凝视着他。
他说。
“那你就,这样好好活下去呗。”
“好好活下去”――这话成为了刺穿阿七的长枪,让她觉得鼻子有些酸楚。虽然自己早已接受稗田家的宿命,并视记录历史为神圣的工作,镇子上的人也对自己万分敬仰,然而,却从未有人对自己说过“好好活下去”这种话。
“活下去”,这个词对稗田阿七来说是多么遥远的存在啊。眼前这个青年竟然能如此轻松地脱口而出。甚至于,他还曾经表示要娶自己当媳妇。多么愚蠢然而可爱的人。
稗田家的女人,没有与人长相厮守的自由。
可如今的稗田阿七,却在青年的话语下,感到这种对自己来说莫须有的自由,变得稍微有点点实感了。
她闭上眼镜,捂嘴轻笑。像是在回应青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是啊……”
那就……试着继续活下去吧。
她这么想。
“那,回去吧,回家。今晚不是有祭典吗?”
“对啊,不能再闲着了,不然会被工头骂的。你刚刚说自己累了吧?来,我背你。”
于是,阿七匍匐在少年的背上,向回家的路走去。少年的脚印,在尚未干燥的泥土上画出一条长长的轨迹。
“真该……对你说很多声谢谢呢……”
阿七的呢喃声,青年并未注意到。
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晚了。
明明没有这种自由,为什么想要去争取呢?
明明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啊。
然而他的话,却令我无比向往,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抛弃这副身体去追寻。
所以……
所以我……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啊……
几年后,阿七成亲了。但丈夫却并不是青年,而是隔壁镇的少爷。这门亲事办得十分盛大,两大镇子里的住户,连同短工们,甚至周围村子里的村民,都收到了请柬,青年也一样。那天,两人喝了交杯酒,亲戚朋友祝贺一番,又请了僧侣做法,一番打经唱法之后,阿七便和这个她连相貌都记不住的男人成为了夫妻。当然,这门亲事里,妻子和丈夫之间并不熟识,两人与其说是两情相悦,不如说是镇与镇之间的“政治联姻”。
青年收到的请柬上所写的日期是三周后,那时候并非农忙,因此青年不在镇子上。他写了一封信把下一年预订好的短工工作给辞了,而阿七的大喜之日,他也自然是没有去的。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听说入了别家的阿七,和丈夫一起回本家了。而另一边,青年家仅有的一片土地,本就没有丝毫肥沃可言,再加上天灾不断,收成欠佳,青年无奈只好再写信到东家去求工作。
当他再一次以做工的身份踏进稗田家大宅的时候发现,除了不见阿七的身影之外,一切都没有改变。
总管免了青年的试用期,毕竟除了阿七结婚那年,青年每年都会来打短工。工头也是老样子,只是白发又多了几根。工头平时对其他年轻工人都十分严格,然而也特别敬职敬业,因此无论是东家的人,还是其他工人,都对他有一种近乎尊敬的感情。之前就是他警告青年“别对东家动歪脑筋”的,而这次见面,他却罕见地露出柔和的表情,私下安慰了青年很多次。
“稗田家的女人,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如今东家已经去了隔壁镇,你收收心,好好干吧。”
工头这么说,并拍了拍青年的肩膀。对此,青年只是默默地点头,没有回应。
自己以后,或许再也见不到阿七了吧。青年这么想。但命运总是出人意料,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会在一年后,在街上偶遇上那个日夜思念之人。
那仍旧是一个有着牛哞和夕阳的黄昏,青年在完成一天的劳作后,默默地扛着锄头,跟在几个老工人身后。
“偶尔也去喝两杯吧?”
其中一个问道。于是走在他旁边的,头发已有些斑白的工人回答。
“成啊,还是老地方?”
“当然,这镇子上可再也找不到那家店更烈的酒了。”
“哈哈哈,没错。那可是天下第一酒馆。”
大笑的那人说完后,突然转过头望着青年。是工头。
“小子,你也去吧?”
大概是想借酒缓解青年的忧愁吧,工头虽然从来不说,但从心底还是担心着青年的。
不过青年却拒绝了。
“我就免了……还没成年呢。”
“是吗……那真可惜。”
可是工头丝毫没有可惜的表情,听了青年的话之后,又转过头去跟那几个老资格的工人聊天了。
青年照旧默默跟在后面,低着头,耳边不时传来工头那豪爽的,但却由于太过豪爽而显得有些沙哑的大笑声。正当少年转移注意力,将视线放到脚下热得发烫的石子上的时候,突然有一袭缀花和服的衣袖,从他视野的余光中扫过。
他猛地抬起头来寻找和服衣袖的主人。也就是在这一时刻,那被三年时光洪流所冲刷到只剩下火星的,那股诚挚的年少热忱,在这一次偶然地擦身而过当中,已有重新化为烈焰猛兽之势。
然而那火焰的光芒只持续了一瞬间。
阿七的眼睛在与青年相照过后,便如同以往咏竹的时候那样,稍稍往下一沉,露出了悲哀之色。青年也默默地低头而去。
但是。
“请留步!”
青年背后传来了声音,如同儿时的风铃摆动时叮咚作响一般清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东家!”
阿七的话没有说完,便被身旁的一位婢女扯住了衣袖。青年转过头来,这才发觉,气色与以前丝毫不爽的阿七身上,唯一改变的或许就是那蹒跚的步伐,以及微微胀鼓的小腹。他立刻明白了目前的情况。
“求求你了,请听我说……”
阿七的声音已有些颤抖,那清脆的风铃声正被泪水抹锈。
“等我转生!我绝对会……!绝对……”
阿七的话没有说完。
“算了,不用了。就这么着吧。”
青年打断了阿七的话,然而,后文却迟迟说不出口。只得挠着脑袋,用笑容蒙混过关。
“你也算找到了门当户对的幸福嘛……哎呀,怎么说,稍微让我觉得有些羡慕。”
阿七愣在了原地,青年就趁着这个空档从阿七身旁走过,背影坚毅而凄凉。
或许,对她来说,这才是最好的结局吧。青年如此作想。自己只是一个不名一钱的农夫,而阿七却是温室里长大的大小姐。虽然自己曾承诺过要买一大片土地,再娶阿七为妻,然而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在几年之内完成约定。
或许,隔壁镇的那位公子,才是阿七真正的归宿吧。
体会到这一层,青年心中不知何处似乎产生了裂痕,就像是刀刃轻划过胸口的划痕,虽不显眼,但却时时从其中渗出血来。这划痕是划在心口上的,因此也刻骨铭心。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它都会发出阵阵隐痛,仿佛在诅咒着青年的过去。
接着,以未成年为借口谢绝了工头邀约喝酒的青年,在第二天早上,便因为宿醉而被工头罚了两捆柴。
阿七这边呢,回到诀别了一年有余的故乡之后,便再也没有和青年见过面。
虽不见面,但毕竟是东家,各种传言自然会像感冒病毒似的四处传播。青年每天都能听到有关东家,也就是阿七的消息。最后一次碰面后过了几个月,他便听到了阿七的孩子出生的消息。接着又是酒席之类的。他觉得痛苦,但也别无他法。后来,不知从何时起,这类消息慢慢变少了。
青年开始觉得纳闷,毕竟自己平时为了心安,主动忽视了东家的事,也正因为如此,有关东家消息的增减,他也是最了解的。这几天,周围的人似乎都刻意不谈东家的事,铁匠家的良子还因为问父亲“阿七姐姐怎么不出来玩?”而被捂住了嘴巴。他也曾问过工头,然而无论问几次,都没有得到答案。
实在耐不住气的青年不惜冒着细雪,一大早偷偷从短工宿舍溜出来,想要去稗田大宅一探究竟。
在转过街角的时候,忽然一发沉重的雪球打到脑袋上,让他面前一黑。回过神来,才发觉刚刚丢雪球的是铁匠家的三郎,这三郎此刻正在他面前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呢。
正当青年准备将三郎打发走的时候,不远处三郎的妹妹良子,已经跟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唱起了民歌。
歌中唱道:
竹之花,
人言其身,
在华彩初放之时,
便已掉落成泥……
“开了花,就只有死路一条……”
“稗田家的女人,也是这样。”
青年不知为何鼻子一酸,片刻后,两行温热的液体划过脸颊。由于天寒地冻,又下着小雪,他觉得那液体比平常要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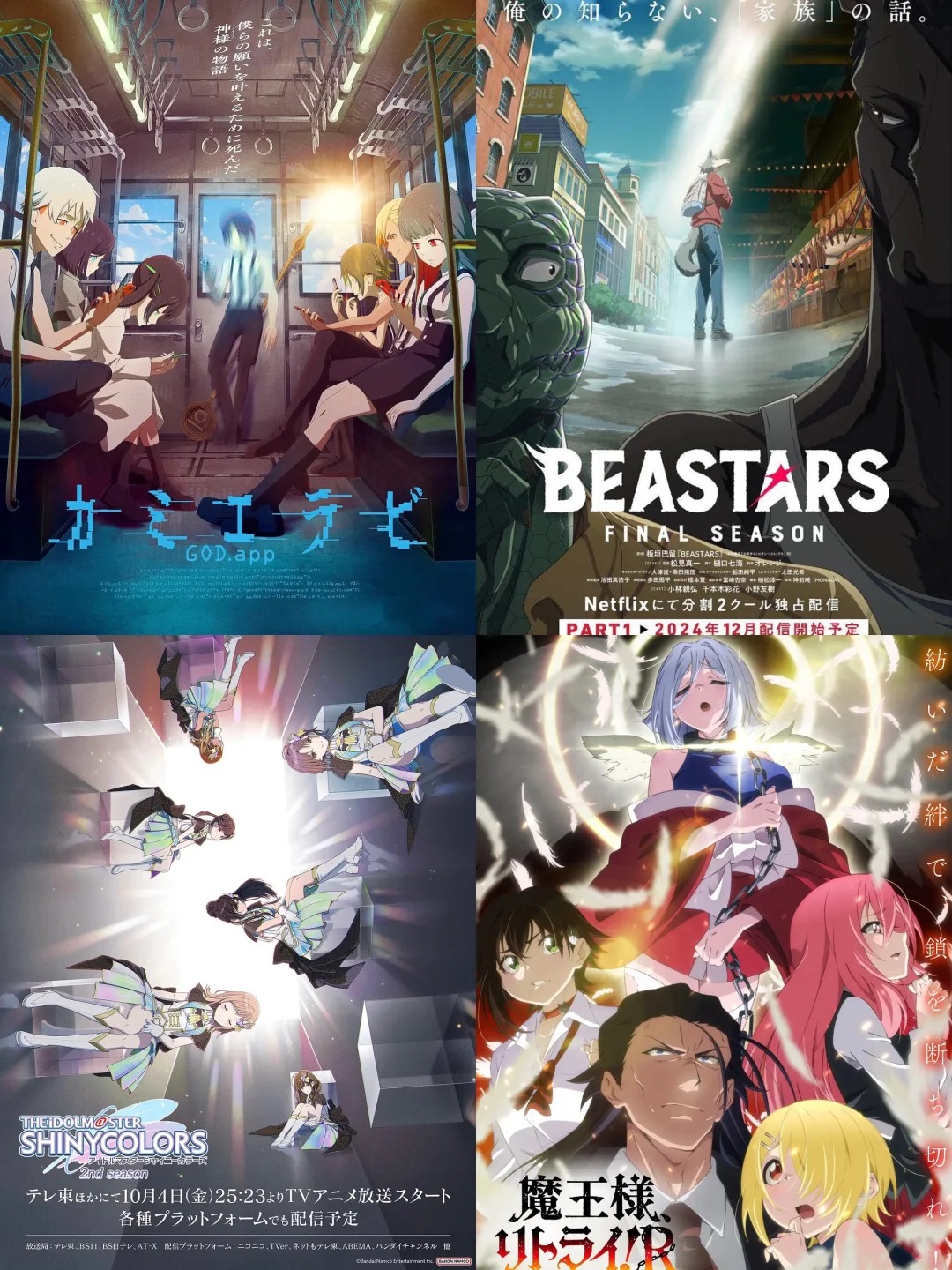







![表情[经典/ganga.gif] - 二次元E站](https://www.ecyez.com/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经典/ganga.gif)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