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泠世
在一段短暂的沉寂后,机舱内积攒已久的负面情绪终于还是爆发了出来。一时间,哭声、怒吼声、劝慰声充满了整个机舱。
在刚刚机长的广播中,我们得知了这样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那就是这架飞机再过一会就要坠机了。我感到视线一阵模糊,没有听清楚机长后面的任何说明。退一步讲,就算是听了机长的说明又有什么用呢?飞机就要坠落了,我们都要死了。因此,眼前乘客们的这些过激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我闭上眼睛,用干燥、有些粗糙的右手揉了揉干涩的眼睛。我感到右手湿湿的,竟然揉出了眼泪。难道我很难受、很委屈吗?我不自禁问自己。在小时候,每当我哭泣流泪时,父亲就会这么问我:你难道觉得自己很委屈吗?
我委屈吗?我不清楚,但泪水已经确确实实地流淌了下来。要说委屈的话我应该是绝对有资格委屈的,不如说此刻世界上几乎再没有人比我更委屈了!从小学到中学六年,熬过了高考,上完了四年大学,多少混到了张文凭,进了一家还算满意的公司,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好不容易得到了假期,搭上了前往外地的飞机。很多事情我都还没有去尝试,去体验,如今我竟然就要死了?
我仍闭着眼睛。由于飞机上光线很好,所以即使闭上了眼睛充斥眼前的也不是无止尽的黑暗,而是带有点点红色的虚假黑暗。我试着回忆我的过去、童年,回想数年以前还在家乡里的情景,回想我的父母、祖父母、姐姐、一些亲戚、街坊邻居。越回忆,我越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我对那些至真至纯的回忆竟然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留恋,而任何还存有健全情感的人都本该对此伤心垂泪,甚至即使变的和眼前逐渐失去理智的人们一样歇斯底里也丝毫不为过。我不由得也为自己的父母感到悲哀,竟然生出了我这样一个狼心狗肺的孩子。
诚然,我刚才确实是流泪了,但我却分明知道那并不是为了父母、为了家乡的一切流的。我知道的很清楚。
那么,刚才我的眼泪究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流下的呢?
“先生?你还好吧。是身体不舒服吗?”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身边轻声说。
我睁开眼睛,因为眼睛尚未适应机舱内的亮度而完全看不清楚她的脸。但从我眼里大致的轮廓和对方那身亮眼的制服来看,对方应该是飞机内的女乘务人员,也就是空姐。事实上,我也猜想不到机舱内的其他人会因为我身体前屈捂着眼睛而特意过来询问我的情况。
在这种所有人都自身难保的绝望处境之下,她竟然还有闲情来关心我,这无疑让我的心里生出了些许宽慰和信心。
“不,我没事。”我说。
但她却没有要退下去的意思。
“真的不要紧?“她再次问道。
”真的不要紧。“我重复道。
事实上,我也真的没有什么事。再说了,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了,有没有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所有人的生命都被人为的增加了上限。在这种时候,就算死亡来的早了几分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几分钟的差别而已了。况且能让人连最后这点时间都熬不过的疾病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
“那好。请问来杯果汁吗?”
我这时才注意到这位空姐还推着一辆餐车。正好有点口渴。
“来瓶橙汁。”说着我的脑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搞怪的念头。
“还收钱吗?”我话锋一转。
空姐一愣,随即绽放出笑颜。我很高兴自己的这个小把戏能把空姐逗笑。
“不,不收钱了。就当是我们公司请你的。”
我接过果汁,故做伤心状。
“我的生命竟然只值这一瓶饮料了吗?”
“放心,你的亲属会受到我们公司很大一笔赔偿的,如果换算成饮料钱的话,可以买到你几年都喝不完的饮料。可买过保险了?”空姐微笑着说。
“买了。我可是很害怕自己会被这样那样的意外弄死的。就像现在。顺带一提,我顶喜欢喝饮料的,我觉得没准我一年就能喝完。”
空姐又被我逗笑了。
“那样你绝对会喝出病来的。祝好运。”
“祝好运。”我说。
祝好运在当前这种境地下总有感觉有点不妥,有种把即将到来的灾难说成“好运”的微妙感觉。在即将到来的飞机事故中能有什么好运呢?最终不过是一飞机的人全灭罢了。我还从没听说过哪架民用航班出事后能有生还者的呢,新闻里也只有打捞到多少多少具遗体的报道而已,全部算不上什么好运。那些报道就算是掺杂了我进去也与我全然无关,就算是我的至亲读到了那篇报道,若是没有通知的话,也绝不会将其与我联系到一起去。及至火化,被丢进大铁炉里面烧成灰,躺到一个小坛子里边去,期间的一切也绝算不上什么“好运”。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说什么祝好运呢?眼前明明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好运的东西存在啊。但是,就连我也说了这句没什么用的话。仅仅是因为别人说了,我便也跟着这么说了而已。
等等,似乎有什么不对劲。打捞?我刚刚确实是用了打捞这个词吧,也就是说飞机坠落到了水里,才需要去打捞的。可我这躺航班分明是陆上航班吧,就算是坠毁也是在陆地,为什么要用打捞这个词呢?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想了想,应该也不是用挖掘,又不是考古。新闻上应该有播过的,但我这时却像失忆了一样怎么都回想不起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日子。算了,就先用“搜寻”代替一下吧。
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东西呢?很简单,因为无聊嘛。我的生命已经仅限这最后的几分钟、十几分钟了,而且还被限制在这狭隘的机舱里,又有何事可做呢?
我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四周。混乱似乎还在继续,而且有加剧的势头。乘务人员显然已经应付不过来了,他们的表现诚然不错,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这种时候还能保持着镇静呢?明明他们也要死了吧,难道我们的命运不是一样的吗?我继而猜想到,他们之所以能保持镇静,一定是因为他们有保命的手段,应用在飞机上来说就是降落伞。他们一定是有着足量的降落伞,能够在最后一刻用降落伞跳伞逃生,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担心会死,所以也才这么镇静。卑鄙的家伙们。我的内心感到了严重的不平衡。真到了那时候,我一定得想方设法去抢一个过来才行。
可是,我不是毫不在意自己会死的吗?明明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事到如今又为什么要去争抢呢?
我坐了下来。在我左边隔着过道的座位上,一个老太太正双手握在一起,闭着眼睛,微低着头,似乎是在祈祷。于是乎我也模仿着做了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应该是某个宗教的祈祷动作吧,是什么教呢?因为实在不清楚,姑且就当成是基督教吧。那我祈祷的对象就应该是上帝,是耶稣。万能的上帝啊,请保佑我……保佑我什么呢?在事故中生还?连我自己都知道这绝对不可能。那还有什么好祈祷的?算了,就随便祈祷些什么吧,毕竟我也只是个在刚刚才决定要信仰基督教的半吊子信徒。我想起了我此行本来打算要见的那个女孩。她今年应该也已经读大学了。明天是她的生日,那今天是几号来着。她的生日是八月十三号,那今天就应该是八月十二号,也就是说八月十二号就是我的忌日。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我突然想起这句话。这句话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说也实在是有趣的紧。这样一来,我的忌日就和那个女孩的生日连在一起了,两者就如同圣诞节与平安夜的关系,这样一来也更方便记忆了。希望她在想起自己生日时偶尔也能想起我,毕竟是在去见她的路上出事的,不每年给我送上两束花可不行。话说为什么是两束?不知道,只是刚好这么想了而已。明明都已经到了这份子上了,我为什么还要去钻牛角尖纠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既然她会每年都送给我两束鲜花了,我就祈祷上帝能带给她幸福吧。
我躺在椅子上,嘴上不自觉的露出笑容。
直至这时,我才像被放在温水里煮的青蛙一样后知后觉:时间竟过的如此之慢!我突然间领悟到了这样的一个常人通常不会了解的事情,就是原来等死也是相当麻烦的啊!
我感到坐立难安。可是,我还没有死,我还活着,那就总是要找点事情做的。虽然就这样在椅子上干坐着似乎也不错,但潜意识里却分明清楚地告诉我我想找点事做。闲着也很麻烦。
于是我想起了一个女孩,另一个女孩。不是我今天原本打算去见的那个,也不是那个温柔体贴的空姐,而是一个我只见过一面的女孩。我看见她时,她穿着一身素色的连衣裙,光润柔顺的头发被绑成一束垂在身后,手里拿着一本暗红封面的大书。我是在登机时看见她的,在看到她的一瞬间她便完全占据了我的眼球。可惜拥挤的人群很久就如同潮水一般将她淹没不见,所以我只看到了那短短的几秒。
她此时应该也在这架飞机上。我再次从座位上起身。这时飞机的一个颠簸险些将我重新扣在座位上,我紧紧的抓住了前座才避免了这一事情发生。颠簸并不是刚刚才出现的,而是早已存在。只是我呆坐在座位上不加理会,所以才会没有很确实的体会到和留下印象。不去想即是没有。我突然觉得自己在神学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虽然我是在几分钟前才刚刚决定信仰的。
我要去找那个女孩,这个念头无比强烈。换做平时的话,我断断是不会如此主动的,但是既然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这一点时间了,那又还会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机舱里的情况既不十分稳定,也没有陷入绝对的混乱。人们固然为自己的生命仅剩下这最后的一点时间而感到愤怒、不满和绝望,但就算被这些负面情绪所支配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是平白无故的把这最后一点时间也浪费掉而已。不如像我一样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说起来,找到那个女孩后我想干嘛?我现在做的事真的是有意义的吗?
我在那一瞬间停下了脚步。但很快,我又克服了迷茫重新迈开了步子。反正就剩这么一点时间了,有意义也好无意义也罢,已经全部都无所谓了。只要敢做就不坏。只要我想去做,那就够了。
现在我又有点同情我要找的那个女孩了。她一定也在机舱里,我正是因为如此断定才像现在这样去找她的。但是这样一来,她便也就逃脱不了和我一样的命运了。在如此锦绣年华偏偏上帝非要让其香消玉殒,我都有些想指责上帝了。
于是我突然又不怎么希望找到她了,可是很不凑巧。无论我怎样分神怎样放松怎样不专心,我却还是真真切切的找到她了。仿佛上帝要在这时让我们相见一般,我只是向那个方向很随意地瞥了一眼,然后视线就牢牢的锁定住她了。素色的连衣裙、绑成一股的头发、厚实的大书。就在我看见她的那一瞬间,我再次把构成她的要素重新又获取了一遍。
我之前对她的同情就如同泡沫,顷刻间全部消散不见。原因无它,自然是因为她看上去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她平静端庄的坐在椅子上,手里捧着那本令我印象深刻的厚实的大书,神色自若的翻阅着,就如同在图书馆里看书一样自在,丝毫不见任何的慌张和恐惧,令人无法相信她正处在坠机这样令人无奈的绝境中。这时候,我的同情便宛如跳梁小丑一般滑稽可笑。
她的邻座没有人,两边都没有,不知是原本就没有还是已经离开了。我鼓起勇气,走上前去和她打了个招呼。
“小姐,你好。”
我希望我的声音听起来不会显得很紧张。
她将头从书本中抬起,眨着眼睛警惕地打量了一下我。我不由得有些紧张了起来。
“你好。”她说。
“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
“请。”
于是我鼓起勇气坐在了她的左手边。
“你邻座的人呢?”我问。
“跑了,不知道去哪了。你呢?”
我不知道她问的究竟是我的情况还是我邻座的情况。略一思索后,我认为她指的应该是我的邻座。
“一样。”我顿了一下。“不知道去哪了。”
“这样啊。”
她依然埋手于书本之中,显然这本书很吸引她,而与我的对话则像是在走程序而已。
“看的什么书?”
于是她把书的背面展示给我看,上面赫然五个大字:战争与和平。
当真好一本大书!在我以往的印象中,一个正处花季年华的女孩断不至于去看一本什么《战争与和平》。倒不是说这本书不好——而是太好了,以至于阅读门槛有些高了,足以将大部分的青年男女拒之门外,转而去读那些书名就很“吸引人”的言情。而这个女孩此时正在读《战争与和平》,这已经足够说明女孩的与众不同了。
“好书!”我由衷地赞叹道。
“是吧?”女孩似乎也大为惊喜。“你也喜欢?”
“不错。可是……恕我冒昧。一般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孩恐怕不会专门在飞机上读一本《战争与和平》吧。”
女孩似乎并没有见怪。
“有人推荐的。最初看的时候也不甚喜欢,甚至还有点疑惑。但是再读了一点后,就完全的被迷住了。”
我点点头。
“当初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里面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女孩问。
“安德烈公爵。”我不假思索地说。
“巧了,我也很喜欢他。那么你恨娜塔莎吗?”
印象里,娜塔莎是个单纯而轻浮的女子。本来先与安德烈公爵有婚约在先,却又被他人诱惑而决定与其私奔从而使婚约毁坏,狠狠地伤害了安德烈公爵。作为我来说自然是无法喜欢娜塔莎的这种行为,但是考虑到她年纪尚轻,又对未来怀着少女那种近乎可怜的憧憬,也就不怎么恨得起来了。毕竟单纯也是她的可爱之一啊!少了这点单纯的话,娜塔莎的形象便不够丰满,也就不是娜塔莎了。
“我想我不恨她吧。”
“为什么?难道你喜欢这样轻浮、朝秦暮楚的女孩子吗?”
“当然不。可是娜塔莎本身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她的种种行为都出自她那可爱可怜的单纯和天真。我又怎么能对她恨得起来呢?”
女孩莞尔一笑。
“你还挺有趣的。”
“也许吧。”
我们的交流又停顿了一会。
“你说要是那时候安德烈公爵没死多好。这样一来也许就能和娜塔莎完婚了。”
“可惜死了。”我说。况且就算安德烈公爵没死他们也未必就能完婚,我觉得。
“可惜。”
我们沉默了一会,随即相视而笑。周围人投来诧异的目光,但我们毫不在乎。真是太有意义了。我想。没想到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竟然还能遇到喜欢同一本书同一个人物的知己。我觉得她一定也有着同样的感受。
“你不怕死吗?”我不无冒昧地问。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这架飞机不是马上就要坠毁了吗?”
“所以呢?”
被她这么反问,我反倒是有点不知所措了。
“也没什么。就是看你好像很镇静的样子。”
“可是就算我现在跳起来歇斯底里,又能有什么样子呢?难道我表现的疯狂一点,失落一点,飞机就不会坠毁,我就能生还了吗?如果真能那样的话,那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哭给你看,可是不管用啊。就算像小孩子一样躲进被窝里偷偷哭泣,也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的啊。”
“没错。”我如实回答。
“是吧。所以我还不如在最后时刻保持形象从容赴死呢。”
“是啊。”
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出其他语句了。真是一个奇妙的女孩!
“那你呢?”女孩问我。
“和你一样。慌也没用,索性就不慌好了。”
于是女孩用书本遮起嘴笑了起来,模样简直可爱极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上这架飞机啊。”女孩说。
为什么?只是刚好在这天拿到假期买到了这架航班的机票了而已。我随即想到,女孩问的可能是我搭这架飞机的目的。
“你呢?”我反问道。
“你先说。”
“凭什么。”
“因为我是女孩子呀。”女孩俏皮的说。
“这可真是一个富有说服力的理由。”
女孩笑了。
“这可是女孩子的特权哦。”
“那好吧,我先说。”
我不太愿意谈论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自认为我做过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极为无趣、毫无意义且十分可耻的。就算是平常最好的朋友,我对自己的事也是尽量的避而不谈,偶尔谈起也只是避重就轻如同蜻蜓点水一般的简单提及,点到为止。事实上如果真要说起我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就必然要牵扯到一件我深藏了几年的秘密,可以的话我想尽量不要提及。但是同时,我又十分渴望能了解女孩,了解她的一些事情。她看上去年龄大概也就在二十左右岁 面容清秀、身材姣好,属于在街上看到时会不自觉回头多看两眼的类型。但是也仅此而已。在那之后,我就会忘记她的身姿、她的相貌,甚至忘记我曾经遇见过她这件事。我想了解的是她内心深处更为深邃纯净的东西,为此我愿意以我的一部分秘密与之交换。我不知道我能否从她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更多我想知道的东西,但我毫不怀疑她拥有着那样的东西。
“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请。”女孩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架势。
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在这飞机即将坠落、机舱内乱作一团的时候,我竟会给一个初次谋面的女孩讲起我过去的事情。
“我是要去见一个女孩。”我十分直白的说。“一个十分有趣、可爱的女孩。虽说她一直声称自己和可爱沾不上边。当然,我也从未见过她的人和任何照片、影像,所以对她的一切都只有一个模糊大致的想象。”
“什么都不知道?即使这样也要去见她?”
“即使这样也想去见她。也许很难相信,但我们竟然关系很好?从几年来与她断断续续的聊天中我也知道了她的一些事情,似乎也能凭自己的主观看法给她贴上不少的标签,像是傲娇、学霸、路痴、交流障碍、蠢萌等。”
“她多大了?”女孩突然问。
女孩再次打断了我的叙事,但我并没有为此而感到特别的不快。
“年龄大概在二十左右,我想和你应该差不多。”我看着女孩的脸说。“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是在大学上大二。”
“为什么想去见她?”
“只是因为想见,好奇,就去见了而已。倒也不是说以前不想见。以前也常想见面来着。但那时没有什么物质条件,出行也不怎么方便。也就一直耽搁着了。”
“现在条件好了?”
我点点头。
“现在条件要成熟多了。我已搬出来自己住,也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不是什么十分体面的工作,薪水也不是很高,但在我一年来的省吃俭用下,还是存下了不笑的一笔钱。想着拿这笔钱带她好好去玩一下,于是得到假期后就登上了这趟航班。”
“她是你女友?”女孩问。
我一愣。这才想起来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未好好说明过我俩的关系,以至于被误会成了恋人。
“不是,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或者说要在那之上或之下。虽然她曾经说过她喜欢我,但过后她便再三强调说那只是朋友上的那种喜欢,可爱的要死。但是尽管如此,能听到她说喜欢我,我也感到十分高兴。”
“那你此行去见她到底还有什么目的?”女孩有些疑惑地问。
“只是想和她见面而已。”我说。
“我说,你该不会就是所谓的直男癌吧。”
我不禁汗颜。她怎么会把我和直男癌联系到一起?虽然我对这个名词并不十分熟悉,却也十分清楚这绝对不是什么赞美的好词。
“当然不是!”
“你不想和她睡觉?”
我不由得脸红起来。事实上,如果我说没有想过那肯定是假的。偶尔、有时也会有那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但那也只是我在某个时刻偶然冒出来的臆想而已。我甚至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能猜想到的东西也只是我根据之前的交往经验判断出来的一种东西,和古人对神明的原始崇拜没有什么差别,就像把氧气倒入空气中一样不可察。甚至连联系到的她究竟是不是她本人,我都不甚了解和明白。
“不想。”我多少有些昧着良心说出了这句话。
“真的不想?”女孩带着诡异的笑容说。
“真的不想。”
“可是你……”指着我。“带着存了一年的存款,匆匆赶往外地,去见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孩。怎么看都像是在网络上买女孩的差劲男人。”女孩装出厌恶的样子说。
“喂喂,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和我这样一个差劲的男人说话聊天啊。”
“因为反正也活不久了嘛。还有战争与和平。”她嘻嘻地笑着。
我也笑了。
“因为战争与和平。”
明明我们的生命都即将要走到尽头了,明明四周已经陷入了不可挽回的混乱当中,明明是这样一个令人绝望的处境,我却能与在飞机上偶遇到的看《战争与和平》的女孩谈笑风生,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缘,妙不可言。
“我想我已经说完了。现在轮到你了。”
“已经轮到我了吗?”女孩竟然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原来刚刚她已经把这个约定忘记了吗?其实我本来是想生气的,但一来我们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多,用来生气着实可惜。二来嘛,她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对她我着实不怎么生气的起来,索性就不生气了。万千怒火最后都化成了一句软弱无力的话语:
“讲吧。”
我把背部放松的贴在了座椅上,做好了聆听的准备静待女孩开口。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很会聆听的。
“既然你想听的话……不过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的你可不能取笑我。”女孩说。
“很差吗?”我倒是完全没有感觉。
“很差。往常不怎么开口来着。”
“我看你刚才说起话来挺流畅的。”
“今天可以说是特例。”
“为我而特例?”
女孩白了我一眼。
“真是自我意识过剩。”
我想也是。对于女孩的毒舌,我似乎也已经感到习以为常了。
“那到底是是为了什么而特例。”
“当然是因为反正时间已经不多了,索性就把我这辈子剩下的、没讲完的、不敢讲的一次性全部讲完算了。不喜欢浪费来着。”
“可讲的完?”
“讲不讲的完无所谓,反正多讲一点是一点。”
“哈。”
把物品的使用价值尽量用完这一点倒是与我相像,我也不喜欢浪费。但是确实如她所说,时间当真不多了,于是我忙督促她回到正题上去。
“事实上,我的目的可远没有你的那么浪漫、瑰丽,仅仅是生活中十分平常的一件小事而已。”
浪漫吗?
她继续说道:“我们家不是单亲家庭,但大家都这么认为。其实只是因为在我们家里父亲主外,母亲主内,所以从小到大我都几乎全是母亲一手带大的,关系也要比父亲深厚许多。她——我的母亲,是一个长相颇佳的普通母亲,我在相貌上受了母亲不少遗传,这点上我得感谢母亲。她上过大学,手里掌握着钢琴、园艺等多种技能,本来也是要出去工作的,我敢保证她一定能有所作为。但是他——我的父亲,用以爱为名的丝线精心编制了一个精巧的陷阱,将我母亲关入了其中。他不许我母亲出去工作,于是我的母亲就如同手工栽植的盆花一样,再也动弹不得,除非枯死,不然别无他法。诚然,父亲每个月都会给我们数量相当可观的一笔钱,足够我们肆意花费,而且向来有求必应,父亲从没拒绝过我们在消费上的任何要求。但这样鼎铛玉石的生活也逐渐让我和母亲忘记了贫穷为何物,我们也不敢想象父亲一旦不再给我们这笔钱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将会如何。于是我们对父亲在外的胡作非为听之任之,我的母亲也从此再未出去工作过。现在——昨天,我的母亲这才终于再次得到了自由。她走了,而我的目的就是回家奔丧。”
女孩稍微停了一下,喝了几口水。
“刚才我也说了,我的父亲是个把束缚他人当作乐趣的坏蛋,因此我在上大学后便如刚长出翅膀的小鸟一样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我的父亲就是那种会在网络上买女孩的差劲男人,这我知道。他很有钱,这成了他束缚别人的资本。也正是他,把这本《战争与和平》当作礼物送给了我,劝我多读书,让我得以与你相遇。从这点上说,我得感谢那个差劲父亲。”
似乎是作为代表结束的动作,她从包里拿起了镜子和化妆盒开始补妆。何以在这最后关头还要补妆来维持形象?飞机坠毁以后,一切都会面目全非的吧。
还有就是,女孩刚才的讲述里有一段是错的,那就是说我们因为《战争与和平》这本书而相遇的事。最开始吸引住我的并非是这本厚实的大书,而是她遗传自母亲的相貌。尽管这本书在我们的交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揉了揉眼睛,仰靠在座椅上。虽说女孩自称说“表达能力很差”,却也能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大致讲清楚了她此行的目的及她父母的事情。飞机上的所有人,都是带着各种一样不一样的目的登上这架飞机的,如今它就要坠毁了。
我感到了些许尿意,想着死前怎么说也要解决一下才行,于是我从座位上突然站起,结果因为起身过猛而险些失去意识向后栽去。
在那会,我忽然感觉到,这一切都是极不正常的。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人在大笑,有人在大哭,有人在向上帝祈祷,有人在尽量维持秩序。世界究竟是怎么了?我们所有人都在干什么?
带着种种疑问,我穿过人群向厕所走去。不出意外的话,这大概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小解了。我甚至还担心飞机会在我上厕所的这点时间里坠毁,那样的话恐怕不太雅观,不太好。可是为什么不好,我却并不清楚,明明一切应该都已经无所谓了才是。
我打开其中一间没人使用的厕所门,正好隔壁的人也正好开门出来,我们就在那一瞬间擦肩而过。凹凸有致的身材,亮眼的红色制服,因为哭过而明显变红的眼眶。关上门后,对着镜子中的自己,我竟久久不能平静。虽然只有一面之缘,虽然那时我因眼睛尚未适应光线而看的并不清楚,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我敢肯定,刚才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位女性,一定就是之前送我饮料的那个女孩。不同的是,那时的她乐观开朗、气色红润,给了我莫大鼓励和宽慰。而刚才与我擦肩而过的她,满脸写着害怕与恐惧,脸色苍白眼眶通红,显然已经哭了有好一段时间了。现在的她,只是个二十来岁正处花季年华的普通女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变化呢?为什么要哭呢?她们不是有着能够逃生的降落伞吗?
我泼水冲了把脸,冰凉的感觉刺激到皮肤,带走了脸上黏腻腻的感觉。一同洗去的,还有一层类似于膜一样的东西。这层膜不知何时起开始就一直粘在了我的身上,直到现在我才真真切切的看见了没有膜遮挡的世界。在冲过脸之后,眼前的一切都清晰了起来,清晰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如果让一个常年近视的人突然间不再近视,也许就能体会到我的这种感觉。而这一切的模糊,似乎都是从那位空姐把我唤醒开始的。
我颤颤巍巍地走回机舱,飞机的颠簸和摇晃从未如此真切地影响到我。因为曾经保护我的那层膜已经随着冰冷的凉水一同消失不见。眼前的一切无疑都是疯狂、歇斯底里、但却又是无比清晰的。那边的男人不是在笑,而是在哭;那边乱砸东西的人也不是因为丧失理智,而是为了转移内心深处更为暴戾的冲动;老人并非因信仰而祈祷,而只是为了祈祷而祈祷。原本看不清、看不懂的一切在这时竟然都能看清了。所有人的行为都是正常、有迹可循的。
我回到了女孩身边,她的两边依然是空的。我突然想起了光亮的一首歌:《右手边》。我仍坐在女孩的左手边。
“嘿。”
我扭头看去,鼻子正好碰到了女孩递过来的几束花。
“满天星?”
“满天星。刚刚一个男人大笑着送给我的。”女孩说。
我怔怔地看着那点点白花,脑袋里好像化成了一团浆糊。
“喜欢吗?”
“喜欢。”我将满天星放在了裤子上。“谢谢。”
“不用谢。本来也是别人给我的。”女孩说。
我已无暇顾及其它,静静地看着裤子上的白花。干净,洁白。耳边的聒噪渐渐远去,这种感觉就像要睡着了一样。
“嘿。”女孩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再次转过头。这次我清楚的看见了女孩微微颤抖的双肩和有些泛红的眼眶。我一瞬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能请你紧紧握住我的手吗?”
“害怕了?”我故意装出随意的样子问。
“害怕。”女孩十分坦诚地说。
于是我伸出右手放到了女孩的左手上,随后与之紧紧握在了一起。女孩的身体随即放松了下来,似乎仅仅是握个手就能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一样。
“对了,能向你借张纸吗?虽说不太可能会还了。”
“纸?你要做什么?”
“写信。”
“写信?还有时间?”
“我只写很短的一点。”
虽然疑惑,但她还是拿出了本子撕了一页给我。纸是女孩子们常用的那种小巧、粉色、带有一些小图案的纸。不大,但我也不需要很大,只需要简单的写上几个字就可以了。
我已经很久没写过信了,我不清楚格式是否正确,但连这也无所谓了。我在左上角提笔写道:致所有人。加冒号。我觉得写的很漂亮,可能是我这辈子写过的最漂亮的字了。我很快驱散了这种想法,继续在下面填了几个大字:抱歉,先走了。我将纸张对折三次,随意地丢到了地上,毫不在乎会被谁偶然捡到或者踩到。
“你指望它能幸存?况且你连名字都没写。”
“这不重要。我只是想写遗书,然后我已经确实的写过了。”
女孩不再言语。
做完这些以后,我放松地瘫在了座椅上,仿佛全身骨架都要软掉成团似的。在今天,一个男人去见所谓的网友,然后不见了;一个女孩回家奔丧,也不见了;也许还有一个女孩,她会待在候机大厅里,但是她永远都等不到来见她的网友了。也许她精心化了妆,也许她早已做足了各方面的物质准备,也许她早就做好了对方会鸽的心里打算。我突然想到,如果得知了我出事故的消息,那个女孩会作何反应?
然而我什么都没精力去想了。闭上眼睛,眼前一片漆黑。我突然有种错觉,仿佛这一切都只是个噩梦,一觉醒来,旁边的空姐还会问我想不想喝杯饮料……
“想什么呢?”隔壁握着我右手的女孩突然问。
“想天堂。”
“天堂里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一片漆黑,然后我在睡梦中缓缓醒来。”
那是永远的一片漆黑。
女孩咯咯的笑了起来。
“你这人还挺有趣的。”
“谢谢。”
我们不再言语,但我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了最后时刻的到来。
要醒来的话只能趁现在了,我想。
我在心里默默开始倒数。
十、九、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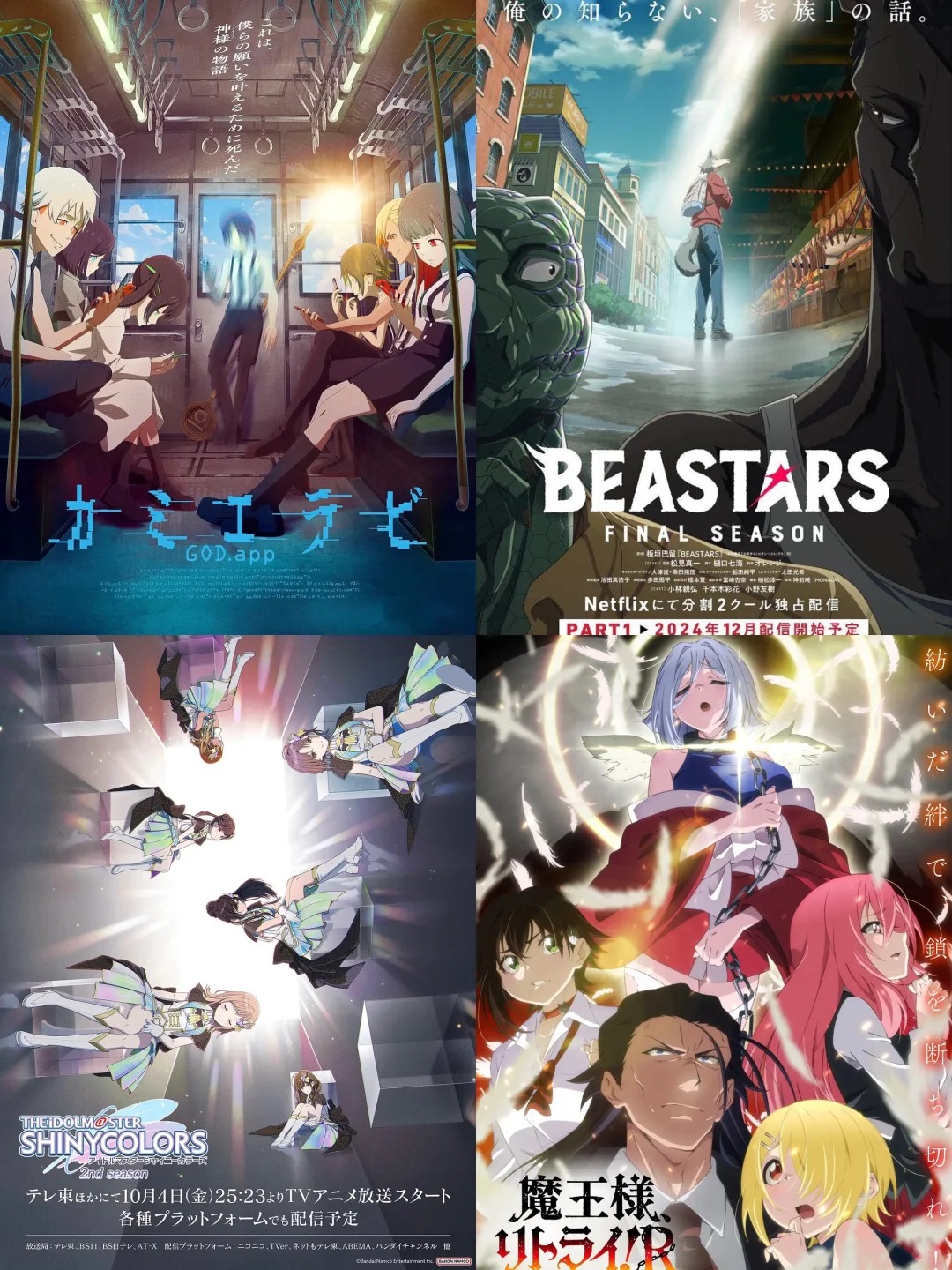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