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净心
如果说,人的一辈子以八十岁来计算,我的人生非常的短暂但若跟那些因疾病或者意外死亡的人比起来我已经非常的幸运。因为至少与这些人相比,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至少是由我自己决定的。
我会得知我已经命不久矣这件事是在高中时期。这个命不久矣的通知突然的来临就像在对我开一个天大的玩笑。我想你不难想象当我听到这个通知时的表情,在逐渐走向好的未来的过程里我被老天爷无情的宣判了「你没有以后」这个未来的心情。
当然,对于我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件事我并不是没有任何察觉,只是没有想到我的身体竟出现了如此大的问题。只可惜当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我曾思考过在死前应该完成什么事,但仔细思考后发现这个年纪的我想做的事情仅凭我余下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
若将我死后想做的事情列出来我想至少可以写满几张纸但我想老天爷也许正是看穿了我的贪心想法所以并没有给予我这么多的时间。
我知道,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时间去上学。我想只要我对父母说出「我想将剩下的时间多花一点在多看一点世界的美好景色上」父母一定会让我马上退学并帮助我达成这个「最后的心愿」。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我期待的,我想至少在我还能活着的时候我想多看看朋友的笑脸当然也不能少了『平凡的同学』。
我与他最初的相遇是在我进入这个班级的某一天。
原本要我来说,像他这种不爱说话,整天一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人应该是跟我这种性格活泼,朋友很多的人八竿子完全打不着的两个极端人群,但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是两个极端的人群所以有了这种跟朋友或者恋人这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我知道说自己性格活泼,朋友很多这种话看起来就像是极其自恋的人才会说的,但我说的这些特征只要是认识我的人想必都会赞同我说的,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嘛。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与他是在分入这个班时就是同学的状态,但作为同学的我或者他都极少与对方交流,不如说正因为我们是两个极端的人群所以更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我想在他看来,我与他不论是呼吸的空气或者是交往的人群又或者连呆的世界可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我与他的关系本应就这样保持到毕业才对但就是在这我毫无察觉的时候老天爷对我开了一个我一点都不想笑的玩笑。
记得那是在高中时期,某一天我因为肚子不太舒服不断往返家里的洗手间与自己的房间。一开始我认为这可能只是单纯的吃坏了肚子所以没太注意,但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肚子痛的不是一般的强烈父母猜可能不是正常的吃坏了肚子赶紧带我上医院检查。
那次是我第一次知道「胰脏」这个人体器官也同时明白了我的疼痛感全部都来自这个名叫胰脏的小器官。
这天检查完,医生开了点药给我并告知我与我的父母过几天来拿检测报告。
我本以为我肚子疼这件事会随着吃药这件事就这么消失但从结果来看,我的猜测真是大错特错。这时我还不清楚胰脏这个器官对人的身体到底有多么重要。
自那天之后,我的身体确实有因为吃药这件事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和但那也只在我吃药的那几天而已。
吃完药后的几天,我的肚子偶尔还是会传来很痛的感觉那时我以为这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体对这个药产生了某种抵抗性但想起吃药后的短暂好转感觉这个猜想应该不对而再次造访这间医院看病。
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我认为医院就是一种人们不得不去接受不幸的地方。记得那是我第一次造访这间医院的时候,我坐在等候厅里等候看病,来往于身旁的人每个人的步伐都是异常的快看上去就像一秒钟也不愿意多待在这里。我一个人静静地等候着我的名字被叫到,就在这之后的没几分钟我隐隐约约的从远处听到了某个人的哭泣声。
那是一种很低沉的哭泣声,我想只要耳朵不刻意去采集这段声音马上就会被身旁各式各样的声音给淹没掉。
我朝身后看去,坐在那里的是一个看起来与我年纪相差不多的少女。看到她的这副模样我走上前去坐到她的身边向她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但对于我的提问她丝毫没有要回答我的意思,只是独自一个人哭泣。
坐在她身边几分钟后她仍然没有要跟我说话的意思。我想至少得先弄清楚她为什么哭泣才有办法进行下面的对话而向她带着的随身物品看去。
不得不承认,在完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从它的随身物品下手了解一个人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她的手上握着被她用力揉成一团原本可能是病例的物体。」
当我向她询问她手上的东西是病例吗时她握紧那团物体的手明显的加重了力度,好像害怕被别人看到里面的内容一样。
「看来那份病例上面写着的内容就是她哭泣的理由了。」
但就在我得出这个结论后我的喉咙就好像突然干枯了一样说不出任何话。更准确的来说,是我的内心排斥了我想说话的这个念头。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我的这股排斥我想说话的原因这是因为眼前的这位少女。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她个人的痛苦通过哭泣声传达到了我的内心但真实情况与这个有点微妙的不同。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觉察到为什么。然而我的身体已经像将这一切都看穿一样对我发出警告但我仍然没有任何警觉的做一些无意间会导致我失意的行动。
在过了大约十分钟后我的名字被医院的广播叫到前往治疗室。
当我离开治疗室出来时那个少女已经离开,剩下的只有失去原本坐着个人看起来已经失去了作用的凳子但就在我感伤这件事时那个凳子上面已经坐上了新的人。
走出医院大门,淡黄色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身上,与刚刚在医院里感觉到的感觉截然不同,相隔一个大门正站在门外的我因为这生命力旺盛的阳光感觉到世界的美丽,但站在太阳下的我虽然没有说出口但看着生命力旺盛这般景象我心生了一点嫉妒的情绪。
在那之后我也不断持续着往反医院与自己家跟学校。
那时就算医生没有对我给出肯定的回答但我也隐隐约约的觉察到我的病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好的事情,我做的最坏的打算就是少活十几年或者二、三十年或者一辈子带着这种病活下去。是的,就拿那天医生对我说的话来说,我的预测有很大程度上猜中了。我原以为,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就医生跟我说的来说我果然还是往好的方面猜了。
我就像是大部分参加某种重要赌博的人一样在参加赌博时尽量下降对赢的期待转而在猜测结果时尽管往坏的方向猜。我明白应该往坏的结果猜但内心里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那一小点不愿意去猜想的猜测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我的逃避让我不得不应对这个结果。
我记不得这是我第几次来到这间医院也不记得医生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将他说的话浓缩大意后大概就是「你的胰脏已经坏死,你大概没有多久可以活了。」
「胰脏坏死?我大概没有多久可以活了?」这……算是什么新型的玩笑吗?
坐在医生正前方的我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失了神。随后医生将视线转向我的父母告知他们我的情况,那时他们谈话的内容我几乎都没有听进耳朵里,不,也许那时的我连将听这件事都给完全忘记了也说不定。
在那天之后,医生推荐我的父母让我住进医院并对我说:观察一段时间说不定能有什么转机。正好那时是我高中临近放假的时期所以在安排上面没有任何问题。
但医生那天对我父母说的话很清楚的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医生很巧妙的用他的说法将我的死淡化为可能而不是肯定,但我自己实际在清楚不过了,我到底能不能有转机其实我了然于胸但我确实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也许我明天、后天或者在隔天我都有可能突然就这么死了。具体是什么时候死这件事我自己也无法预测,只是会死这件事我已经很明确的明白了。
为了防止父母他们过度担心我,我听取了医生的建议住进了这间医院。
第一次走入医院的病房就是在今天,这个医院的病房与我曾经在书上看到了解的病房有着很大的出入。像是书上会提到的病房模样在这里几乎没有体现,只不过想起来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那是书里说的嘛。
入住医院这件事我并未对同班同学或者玩的比较好的朋友们提起,就连放假时期她们的邀请我也都以「有事情要办没办法去了」来一一回绝。
住进医院对我这种天生有点坐不坐的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的环境但与此同时我在这里又交到了一位朋友。
诚如我刚刚所说,我在这间医院里交到了一位朋友。她的到来让我足足惊讶了有好一会,我想对她来说也是一样的吧。
前段时间我看见的那位少女,如今正坐在我旁边的床铺上。这一次她的到来让我很快的就明白了上次我没能知道的一个问题的答案。
那时我曾想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足以让她哭出来然而当她入住这里后我就明白了她哭泣的理由。
「你也没多久可以活了吧。」我对她说道。
「这点,你也是一样吧。」那天是我第一次听见她说话。她的声音有种很纯净的感觉,听起来就像是没有掺杂任何东西的溪水不断游走一般。
「原来你会说话啊。」
「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第一次看见你时我以为你是个不会说话的人呢。」
「自变成这副模样开始,我就很少与人交流了。」
听完她的这段话,一想到我是个为数不多能让她愿意与我说话的人,看来我的魅力还是很高的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的有点小高兴。
「你还有多久可以活?」她看着眼前的墙壁看也不看我这里向我发问。
「不知道,只不过死是肯定的了吧。」
「你连自己什么时候可能死都不知道吗?」
「是啊。如果我连这种事都能预测到的话我就不会在待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了吧。」
「你认为待在这里是浪费时间吗?」
「是啊。因为你看,像我们待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未知,有趣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吧?」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这里还有可能加速我们死去的时间。」
「也许是这样吧,但是在死之前我想多去一些地方看看。难道你没有这种想在死之前再去看一次的地方吗?」
「你说的那种地方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在看另外一个世界的生产物一样。」
「原来如此。」
「你对活着这件事不抱有任何希望吗?」
「以前我想我对生活至少还残留着一点希望但现在我想我已经不期待了。如果要说为什么的话,让我们这种马上就要死了的人再去期待希望那不是太残忍了吗?」
我无法反驳她说的话,如果不了解状况的我确实有可能会告诉她不要放弃希望这件事但与她站在相同立场的我知道,她说的一切都极为正确。
劝告他人追求幸福这件事,是真的为了他人好吗?我是否应该多站在她的立场上代替她思考思考。
「她刚刚问我,我什么时候会死。难道她已经很清楚的感觉到她什么时候会死吗?」
当然这个问题我并没有问出口,因为我感觉只要一旦将这个话说出口就像是开始否认某个人存在过这个世界上的痕迹,那种感觉我从心底里感觉讨厌。
想到这里,说实在感觉并不是很好受。
「对了,等等要一起吃饭吗?」
「……吃饭?」
「是啊,因为你看也差不多到吃饭时间了。」
我刻意转移开话题让她不要觉察到我心里的微妙变动。
在那天之后的半个月里我们时常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聊一些平常大人绝对不会允许我们聊的内容。
这天也是如此。在这半个月里我与她逐渐形成两个人一起讨论或者她单方面说我聆听或者我说她单方面聆听这样的默契。可也因为这样我到她说出那句话前我都以为一切如往常一样没有任何改变。
说到底,与她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逐渐忘记了我们两个是身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里,也忘了关系的加深对我们来说只是残酷现实前的一股美好幻觉,我们根本没有做好承受美好幻觉后的残酷所以一旦当超出自己预想事情的发生我一下就乱了方寸。
「我准备回家去了。」她对我说道。
「……回家?」
是的。家里发生了一点事情我得回去一趟。
这样啊。那你快点准备回去吧。
嗯,但在离开之前我想多跟你说几句话。
要说话的话以后还有机会的吧?快点回去处理事情吧。
这时我还未觉察到她话中真正的意思。我只是满心想着等她重新回来我们应该聊些什么。
那天如果我能稍微再留意一下她的表情应该都可以觉察到她的异常以及她说话态度上微妙的不同。如果要形容的话,那就是一种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的人特有的一种说话方式,如果不是跟她相处了这段时间我想我也看不出来。
在她离开后的隔天,在隔天及大后天甚至到我马上就要出院时她都没有要回到这里来的意思。
我想,她是身体有所好转了所以不用在回到这里了吧。
就在她离开后,没过半个月我也因为学校要开学而向医院申请出院的事情,但就在这个时刻我也接到了医生送来的好消息。
根据医生的说法,只要我坚持服药物日常的生活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关于我能靠这个方法活多久他却没有任何说法。
多亏了药物的帮助,我成功脱离了这段住院时期但离开这里时我自始至终都看着那张曾经有她痕迹的床铺只不过到了现在那张床铺已经换成一张全新洁白没有一丝灰尘的床单。
我跟她的关系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
我想你不难想象,这样的关系在你或者我的身边已经有太多,来往的人数多到有时我甚至会搞不清楚谁是谁只能凭借它留下的某种东西来回忆这个人的存在,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的人我想就算我不想忘记而再三回忆但始终都会被我遗忘。
所以为了避免被人遗忘,我一定得在死前给某些人留下点东西方便让他回忆我呢。
这是我住院时期遇见她的故事,是我未留在『共病文库』上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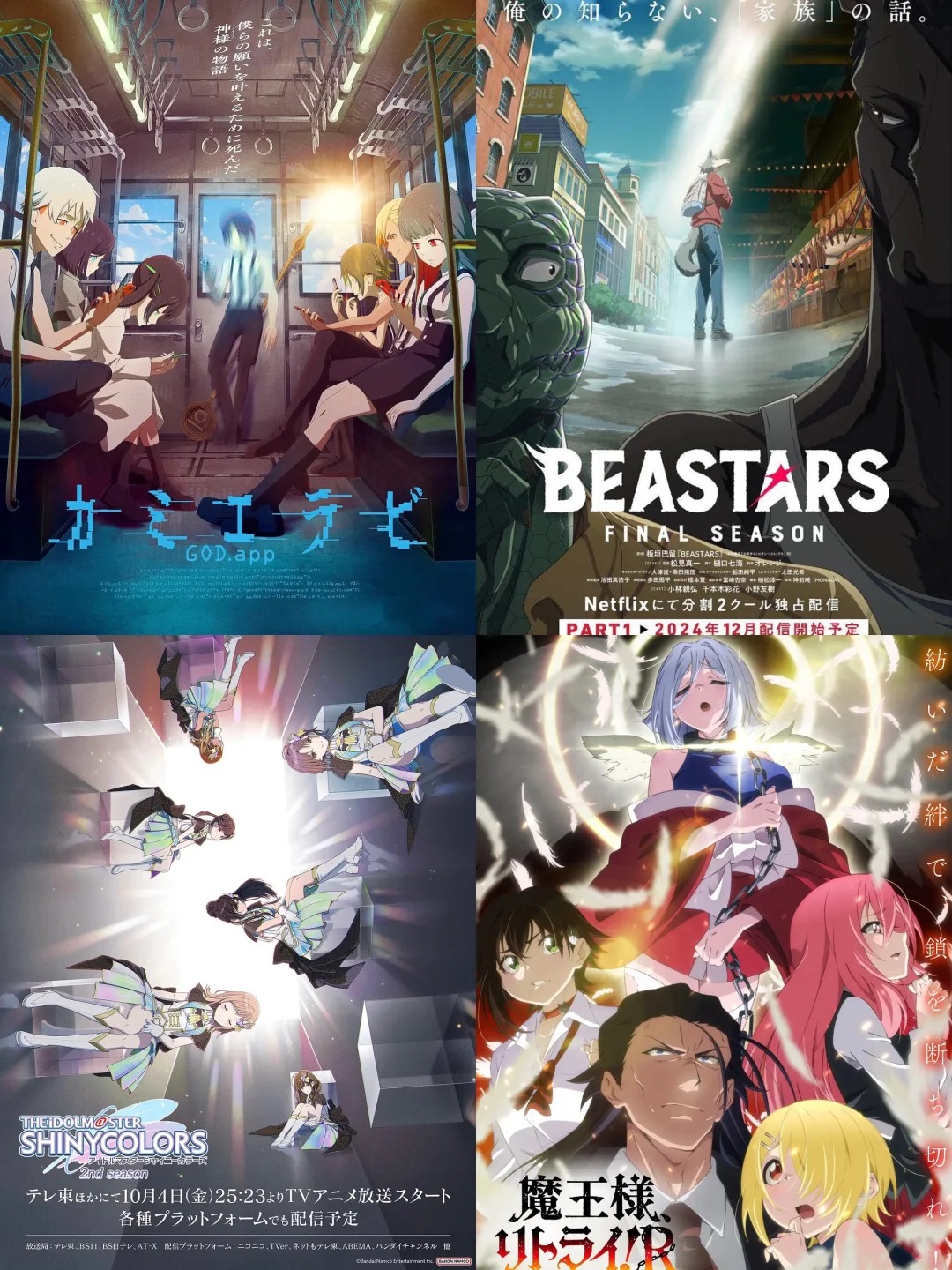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