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invisible cat
01
听说人在将死之时会出现走马灯的现象,人生的经历以一种美好的形象倒放过来。我前三十年里会回想起怎样的故事呢?我想一定就是它了。那个故事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十年过去了,这个故事长出了翅膀,跃跃欲试地像挣脱我的保护,飞向我不知道的远方,它不将属于我了,换句话说是时候该说出我的那个故事。
十年里我成长了吗?我想我没有,如同十年前那时的我想着十年前孩童的我,自己问自己“你成长了吗?”一定也是否定的回答。我是在说实话,经历事故的我,明白了道理算是成长了吗?回到个人的本质上,我并没有成长,只是单纯地经历了。
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是happyending这样认为的读者就大错特错了,如同这个世界一样,事物不是用好坏来区分的,这个故事也不是好的,但绝非是坏的,它既不会鼓励你,但也绝非消极你,因为它只是一个故事罢了。
说到故事,人们会把艺术性的虚构和故事联系在一起,自然我所讲的故事有着谎言的成分,但也是为了使得故事在某些方面比真实有着更接近真实的地方,人们总是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往往忽略看见的真的就是真实的问题,你可以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不不必认为故事传递的东西是虚伪的,这就是故事的魅力所在。
很多小说会讨论幸福理想,它们会在故事的尾声出得出“幸福是存在着”“有理想真棒”的结论,然后读者就满意地闭上书本陷入回味中,我也常常思考这些问题,怎样才算是幸福,怎样才能才算拥有梦想,我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使我信服的回答,所以我想重新讲述这个故事,为了在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回答,十年来,我做了什么,我是否幸福?
十年的临近立夏的星期四,蝉开始鸣叫,空气燥热起来,故事毫无征兆地发生了。
02
我从漫长的午觉中醒来,脑袋空空的,我想到了鸽子,想到他修长的食指和中指优雅地夹着末端红色的香烟,他吸了一口,缓缓地吐了出来,说:“在我所遇到的事情中,无非就是去做或不去做两种,不去看它们的结果,就事情对你的意义轻重来说,做和不做都差不多,得失利害只是对于事情的本身而已,而事情的重要与否取决你,你是否随心去做还是不去做,你想去做,就有做得必要,不想去,就没有去做的意义,仅此而已。”他的口吻还是那样的玩世不恭,嘴角上扬,烟雾遮住他的眼睛。
我站了起来,在自己三坪间大小的租房里伸了伸腰,走向冰箱,拿出一罐啤酒,轻轻一拉,兹拉的泡沫声响起,啤酒花从拉环口出跳动出来,我走向阳台,靠在栏杆上看着风追着云。
毕业之后没能找到工作,蜗居在租房里整天看看书写写故事过日,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我选择这样地生活,但这并非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只是在逃避而已,逃避就职的压力,逃避成为社会人的压力,人是需要身份的,身份会带来压力,有了压力人不会轻飘飘,轻飘飘的生活会使你忘记活着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我感受到了,所以我用酒精和尼古丁麻醉自己。
鸽子在自杀前一天来我的租房来看我,他喝着啤酒,对我说:“你这个人与幸福无缘的,不是你不能够幸福,而是即使抓住了幸福,幸福也会离开你,你会怎样活,活得好不好,其实早就注定了。”他说的话总是让人讨厌,但他本人却不让人讨厌,他总是能抓住事情的实质,然后简洁地说出来,那时我还是一个每天瞎忙的大学生,只是很能写东西,到处参加比赛,我觉得未来很宽敞,只要自己努力地迈出步子就可以了,写不出东西归咎没有灵感,得不到奖怪没人体会我写作的精髓,而鸽子在那时就给我定下不可能幸福的结论,而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不久,有人发现他在自己租来的桑塔纳里开煤气自杀了。
他的话就像无形的手指引着我的人生,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极限。
我写的东西和说的话都是谎言,所以没有人信任过我,我的作品也感动不了别人,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已经成为一无是处的废人般的存在。
我喝完这罐啤酒,轻轻抛出漂亮的弧线掉进垃圾桶中,这时太阳西斜,红色点缀白云的边缘,我出了门,走出了街道,走上河边的水泥路,有几个社团里的学生跑过,几个孩子在河边水泥台上打水漂,我慢慢走着,天空从西边点起燃烧的火焰,走到熟悉的长椅,那个孩子和往常一样坐在长椅的一端,她在用速写本画着画,她画得很好。我在长椅的另一端坐下,从口袋里拿出香烟,我看了一下她,她也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收回去了。
“香烟很好吗?”
“怎么说呢,可能只有大人觉得苦的东西是种美味吧。”我很难定义我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大人,如果严格来说,我还成为不了大人。
“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大哥哥你做什么工作?”
“我没有工作,现在就是混日子。”
“我们的英语老师结婚了,马上就生小宝宝了。”
“是嘛。”
“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的,是不是忙忙碌碌就是好事?”
“不知道,做工作不代表工作有趣,不说不代表不理解。”
她开始动笔画画,嘴巴念叨着细语,眼睛蒙上一层纱。
我凑近看她在画什么,她在画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少女手中捧着向日葵站在高岗上,下面是一大片的向日葵田,她画得真好。此时我们面对着西边,逆光的原因,她的轮廓和面容被模糊了,晚风吹打着她的衣领,她的过肩长发末端染上金黄色,她像在思考一个问题,她的脸上有着光影印记。
我和她相遇是一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季里。
我穿着厚实的呢子大衣,围着红色的围巾,走向自己的租房,我的右手扶着一大袋食物,左手刷着着手机,天下起了雪,堆积在地上有一两厘米厚,我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不是,有个穿睡衣的女孩在一个民房的门口,她双手来回搓着,口呼着气,腿怕冷地颤抖着原地踱步,我注意到她,步伐放慢靠近她。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别人惩罚自己的女儿与你何干,快走你的路。”
心中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我的身体僵直,头直视着前方。
“你自己连自己都帮不了,怎么能够帮别人,光活着就已经够辛苦了。”
我就是这样的人,自己的事情我都筋疲力尽了,别人怎样都与我没什么关系。
我走到她的面前,一步,两步,我走了过去,我是一个胆小的人。
看不到了,心真的就能平静了吗?
我想到了鸽子,想到了二十年的人生,以一种回放的形式重新再现了一遍,这样就可以了吗?
你满意了吗?
你是永远不可能幸福的。
“等下!”我朝自己的心呐喊道。
我转过了身,走了回去,走到了女孩的身边。
“这么冷的天,怎么一个人在房子的外面,多冷。”
她用着惊诧的双瞳看着我,我是个奇怪的人,这我知道。
她没有和我说话,我独自说:“这样的父母怎么能这样,把女儿丢在这里。”
“冷吗?”
我取下围巾给女孩围上,她退了几步,她在怀疑我是不是坏人。
“我在这个城市里算得上是一个人畜无害,虽然我有些奇怪,但就论本心来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这一点你可大可放心。””我拍了拍胸口。
她口中说了些什么,细若游丝,在空中飘荡着。
“说什么,让我听听;”
我露出尴尬的笑容走上前去。
我听到了。
“不可以和陌生人说话。”
“陌生人?”
“如果我们互相知道名字,就不算是陌生人了。”
“我的名字叫王俊宇,你的名字叫什么?”
“陈——文君”她小声地说。
“这样我们就是朋友了,就不再是陌生人了。”
她笑了,小孩的笑颜发自内心的,闪着光芒。
“大哥哥,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这我知道,我确实是个奇怪的人。”
“我也是一个奇怪的人,父母都是这样说的。”
“奇怪也非一件不好的事,说明你与众不同。”
我给文君围上了围脖,看样子一会她还是不能回到家里,我的房子就在附近,我带她来到我的住所,她的腿上有些伤,我简单地给她处理的一下,温了一杯牛奶给她喝。她双手合十,说“我开动了”,然后开始喝,说明她的家教很好。
我套了一件大衣给她披上,用无线音箱播放着轻音乐,我找到《小王子》给她看,自己随手捡起一本书在女孩的对面坐下看。
时间在氤氲的暖气中流过、
我的脑中闪过那句话。
“你是永远不可能幸福的。”
但这些都无所谓了。
事后我送女孩回了家,但我没因为做了一件好事而喜悦,我担忧这个孩子的未来,而这份担心随着和她的相处中越发强烈。
她停下了笔,她的脸充满着阴郁的情感。
“每个人都这样,可不可以不这样呀。”
“……”
我该用怎样的表情面对这个孩子,用怎样的话语安抚她,我想,以我的身份和能力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什么都做不了,如同当时知晓了鸽子要准备自杀那时,我也束手无策,让唯一的朋友死去,我心生愧疚,可这时又有什么区别.
我坐在她的身旁,但却远得像天边.
我选择沉默.
“很多时候是不由自主的,但是-”
我哽咽了,说不出乐观的话语.
我做的只是悲伤地坐在她的身边.
她那样的家庭,那样的生活环境,作为一个外人来说,我是怎么都难以插手的.
她站起来,走向云投影下的阴影中,回头看着我.
那个眼神穿过漫长的路程似的来到我的双瞳前,她悲伤地说:
“可不可以我去死呀。”
我的脑袋仿佛被木棒揍过一样,我惊吓地站了起来,接住她悲伤的回眸。
一架飞机飞过我们的上空,留下长长的飞机云,轰鸣声从天空中落下,我想挽留她,但她要回家了,她家有着严格的门禁。
她走进了建筑的影子里,再也看不到她了。
我看着河面反射夕阳的最后时刻,大地进入了夜的世界,我鼻子有点粘滞感,抽出一支烟,费了好大的劲才点燃烟,但还是无法平静自己的心。
飞鸟飞过河对岸上的空中,留下夜晚的号角。
03
“家里蹲,给支烟。”
阳台隔板对面传来声音,她是艺术大学的学生,她不习惯和他人睡在一起,就在学校外面租房住。
我抽出一支烟伸过去给她,她接住,咔嚓点燃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
“你管我。”
“你真是一个有趣的人。”
“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怪人。”
“毕业什么也不做,靠父母吃饭,整天在房间里看书,你打算这样生活下去吗?”她吐出的烟雾袅绕升起。
“我当然不想这样生活下去,只是现阶段我只能这样吧。”
“如果是我,说不定也会这样,我没有资格说你什么。”
“这点你还是很自知的。”
“我也好不到哪去。”
由于隔板的原因,我看不到她,她也看不到我。我能想象她戏谑的嘴角,我吸了一口烟,看着午后的阳光抚摸着的城镇,远处白色的建筑闪闪发亮。
我是否也想过死呀。
我自己问了自己。
自杀这种想法我还真的一次没有过,虽然我是一个阴暗的家伙,小时候也遭受到不算严重的欺凌,活到二十二岁时,自杀的事一次都没曾想过,不管到了何种地步,我都不会选择去自杀,这不是什么“自杀式懦夫的行为”的一致表态,而是自己对活着的一种希望,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所以我还不能死这种感觉,当然也没有这么宏大,单纯的就是死是解决不了问题,但我想到了鸽子,我刚说的话就缺乏证据支持,只能说我是一个不想死的人,这不代表我是一个乐天派,我只是简单地不想死而已,与其说坚强地活下去,苟且偷生更适合我这样的卑鄙小人。鸽子的死在我的世界里如同旋风般将我的一切卷得天翻地覆,在生与死之间,我不停地徘徊着,彷徨着,如迷途的羔羊,我找不到答案,我现在的状况既不像活着,也不像死着。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问艺术生。
“我嘛,我什么都不想成为。”
“你真没有梦想。”
“梦想是一个虚构的词语,有些人就喜欢嘴上挂着这高大上的词来彰显自己的高尚,真正的梦想是艰辛的,不是五颜六色的,而是压抑的灰色,经常说“为了梦想””的那些人更本就没见过梦想,只有实现梦想的刹那才有一点点的喜悦感,之后就是沉重的工作和乏味的应酬,如其追求梦想,不如看着电视,看那些所谓追求梦想的人奋斗来得更好。”
“你说得真消极。”
“我什么都不想当,什么也不想成为,我没有欲望。”
“我也没有、”
“你不是说你想当一个老师的吗?”
“我有和你说过吗?”
“有呀,你忘了。”
“我说我想当个老师,说出这句话就仿佛是对我的背叛。”
“你是一个没有欲求的人是吧。”
“是的,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当自己受到关注时,我会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焦急地冒冷汗,心想“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早知道这样就不这么做了””,会不知觉地做很多傻事,我没有能力成为受人关注的人,我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看书,没有欲求是我的特点,或许是件好事,也或许不是件好事,但这都无所谓了。”我拿起啤酒啜饮了一口,说道。
“看来有什么样的故事,说来听听。”
“你想听吗?”
“为什么不,观察你这个怪人也是我生命中的义务呀。”
“说得我就很怪一样,难道你不怪吗?”
“是呀,我是很怪,怪人俱乐部,有你也有我。”
“我以前是篮球队的,初中那会我们学校进入了准决赛,全靠我的功劳,我不是很想强调,我的篮球技术是数一数二的,但这都无妨,无论老师同学都对我给予厚望,那时我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或许到现在也可能没有什么进展,我开始害怕了起来,该怎么说呢,我对期望有种厌恶感,我讨厌他人的视线,尤其是信任的视线,我感觉“怎么会这样””“”“被他人信任好麻烦”,我就喜欢敷衍和逃避,比赛当天,我做了相反的公交汽车,去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在餐厅吃了一顿我一生吃得最饱的自助餐。结果理所当然,篮球队以大比分差距落败,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之后我被人带到隐蔽的角落打了一顿,随后的学校生活,没有任何人理过我,我反而安心下来,是的,我就是这样奇怪的人。”
“这有什么呢,我来说说我的好了。”
“你说。”
“我很早就开始交男朋友,如果说起人数,我交的男朋友快集齐十二个星座了,这不是夸耀自己的阅历,只是为了想说我遇到的这个男生,他是我人生的特例。我虽然是个开朗的人,但谁都不知道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我也从来不给别人看我真实的样子,我就这样带着假面和这些男生交往。我很懂交往的技巧,拿捏分寸才能掌握恋爱的主动,但总会有个特例,我遇见了他。“
她缓了缓,看来烟抽完了,她说:
“有酒吗?”
“你还真不像一个学生、”
“你也不像一个大人。”
我回屋子拿来冰箱里冰镇的啤酒,递了过去。
她喝了一口,说: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一场社团联谊上,他们是文艺社,我们是美术社,虽然我经常画画,但我说真的不喜欢绘画本身。他拘谨地坐在角落里,在联谊会上,引导气氛的人就像把他们的脸印在A4纸上恨不得贴在你的脸上,所以我讨厌这些人,反倒安静出奇的他引起我的注意,我在走廊上和他说:“一起出逃吧””,于是我和他逃出了居酒屋,但发现没有地方去,只好在一个公园里坐在一起,他微微笑了笑,在自动贩卖机边买了果汁饮料,他的笑脸很好看,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主动和他交换了联系方式。我那时决定该和他交往,那时暗暗下了决心。”
我歪斜着头,找个舒服的姿势靠着栏杆上,聆听她的故事。
“他是一个怪人,他什么都表现得不关心,谁也不知道他在乎的是什么,我以为离异的家庭都会这样,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总是不注重修饰,穿着很随便,仿佛就是他本人的样子,那份讨厌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喜欢,我就是喜欢上这样的他,我主动地和他说:“你需要一个女朋友”。他浅浅一笑,低头看他的书,你猜怎么,我顺利成为他的女友,好像什么都自然而然的,但我觉得一切都诡异极了,巧合透了,我很多时候猜测他是否真的爱我,使得这场恋爱像躲猫猫,如果说我是一个戴面具的人,他就是那个面具拿不下来的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我和他是一类人。我隐约感觉我和他是不会长久的,时间会将事情的原样呈现,直到那天的到来。”
“那天,期末考试结束,我和他坐上铁皮公交车去我们都不知道的目的地,我们的旅程没有目的,只是去附近的小镇走走,碎阳光撒落在公交车内,车窗外的麦田飞速地掠过,我们相互依偎着,睡意在我们头上打转。
我们在一个古镇下了车,青石街道里传来热烘烘的气息,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强烈无比,我不得不说了出来,我说:“我想要一个气球。”他惊讶地看着我,我就这么奇怪,有时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说不合时宜的话,这些很难用逻辑来解释,我就是这样固执地想要一个气球,他确信了我的固执后,和我开始寻找气球,在这个古镇里,我们去了每一个角落,学校附近,繁华的老街和没有人的广场,但买气球的人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不存在,我说:“你有没有很想要的东西?”
他说:“没有,人生里或多或少的东西有或没有都不重要,你想要的气球,过几天,泄了气,就会变成破塑料。”我们在一家小卖店停下,我撕开他给我的冰棍,他走进小卖店的影子里,和老板说了一些话,只看见他和老板走进一扇门里,出来时手上多了一个气球,是的,是一个圆鼓鼓的飞在空中的气球,我站在屋檐下,看着他一贯的微笑心里开始害怕,我退了几步,阳光阻隔了我们两人,他走在我面前,给我系上气球,可是,一瞬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还没有感受到气球的满足,绳子就生不知鬼不觉地从我的手中飘走,我们谁都没能抓住飘走的气球,只能看着气球越飞越高,张开起龟裂的嘴唇。
我远远看着气球飞走,我也只能这样做,那是淋着橙汁的下午,一束鲜明的孤独无助的气球在空中漂浮着,我只能感受它离我越来越远,我突然感受到一阵轻松,它飞走了,在那个特殊的时机里,我选择了放弃,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那以后,我和他分手了,他百般地恳求我不要离开他,但这次我心铁定了选择分手,没人能永远拥有某物,只有在合适的时间放手才是正确的选择,至少回忆起来会被满山遍野的遗憾和眷恋所打动。我就像那个气球,选择挣开他的怀抱,越飞越高,我希望这样,我也愿意这样,这样故事才有趣呀。“
她吁了一口气,接着说:
“我是个奇怪人,我开始明白这件事,仿佛幸福是和我无缘的,我无法抓住它,它也无缘于我,我只能在美好的回忆中自我感动,昨天的我,前天的我,一年前的我或十年前的我,都是我,但也都不是我,到底哪个才是真的我呢?我不知道,当初和他分手,我到现在为止都不觉得后悔,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事,我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留在他的心中,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过得好不好,这些已经与我无关了,是的,很多东西都与我无关,我又何必在乎呢?我只能做自己而已,是不是很奇怪呢?”
你是一个奇怪的人,我们是同一类的人吗?”我没有底气地反问她。
“谁知道呢?”
对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她说,我要去趟学校,再见了。
我不知道她现在去学校干什么,但这与我无关,所以我说,再见。
远方的山峦若隐若现,阳光开始让人焦头烂额起来,河岸吹来沁凉的风,电线杆上的蝉知了地叫,我回了房间,睡意上来,我躺在床上,不一会就睡着了,我梦见了鸽子,是的,我梦见了我的友人。我很惊讶我自从他死后没有一次梦见他,这次在梦境中与他相会不得不说是种暗示,不得不说他希望他以这种方式出现。
04
我在梦境中,我站在电玩城的门口,天花板油腻泛黄,日光灯闪烁着,成排的电玩机台发出电动的声音,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在电玩城中徘徊,我走了进去,看到鸽子坐在高脚凳上,用手拄着电玩机台的框架抽着烟,他眯着眼,像一个微微喝醉的人一样。
“那个女孩-”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但心想鸽子已经死了,这个人就是我心中的映像,他对我什么都了解,在他的面前我是透明的。“那个女孩说想去死。”
“这种事情你来问我呀?”
“的确,你不是能帮助我的吗?”
鸽子离开高脚凳,走到我身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带我去能联机的电玩机台,他说:“你想帮助她吗?”
“我也不知道。”
“你要清楚,谁也改变不了谁,人是没有这个能力,如果说能改变他人的能力的存在,那一定是神的力量。”
“这个我清楚。”
“你是一个不能得到幸福的人,因为你从心里就根本不渴望幸福,我说得是吧。”
“……”
“和我玩几盘吧。”
我们把硬币放进尽是磨花痕迹的机台里,选了一款游戏,开始了对战,两胜三败,考虑到鸽子的水平,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做事情总是三分钟的热度,不会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任何的行业中,他会对忽然扫兴觉得“我在干什么呀”的瞬间感到害怕得要死,以至于他兴趣广泛,但都不精通。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跟他相处颇久,但他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相反,他却很了解我,他说的每一句有关我的话都出奇得准,我把他当作灯塔来看待,虽然他不愿意我这样看待他。
“到这时候了,我也不能总打击你,你很清楚你是一个怪人,这点上你很聪明,你想做事我没有资格说来说去,正确的选择不代表正确的道路,这点你要记住了。”
“那我该怎么做呢。”
“你怎么做是你的事,我只不过活在你的世界里的影子,我不能替你承受,甚至不能分担你的悲伤和痛苦,所以你要自己去做,去想。”
他在自动贩卖机前买了两罐咖啡,一罐给了我,自己打开汩汩喝了一大口,他说的话以不正经的口气,但说出来却总能让人严肃对待起来。
梦是没有脉络的,我前一秒在电玩中心,后一秒在海滩边上,鸽子还在我的身边,他说:“你知道吗,海对面有个小岛种着向日葵田,快到夏天了,你可以去看看。”
“向日葵。“
“向日葵的其中的一个花语是勇敢地去追求想要的幸福,跟你很般配,不是吗?”
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画面,在星夜之下,向日葵没有关上,反而绽放着盛开着,漫天的星斗如诉如泣,向日葵田起伏着风的形状。
“你什么时候能变成一个能够幸福的人。””
“这种东西怎么都好。”
“你不在乎吗?”
“不在乎。”
“等到时候,你会在乎的。”
我在黑暗中踩着某个东西,轻轻滑落,我回到了现实中。天已经黑了,我听到了有人在敲我的门,我怔怔看着天花板,不去理它,过了一会,声音有响起来,我不耐烦的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看,是那个女孩。
她来找我,我想她早就知道我住哪里,过来找我玩吗?
“文君,你来了。”
“我有事找你。”
05
她坐在我的床上,我双手拿着盛有果汁的玻璃杯,我将右手的杯子给了女孩,自己喝起左手杯子里的果汁。
她背着书包,看样子是刚放学,书包的右口袋装着用蓝色袋子裹着的竖笛,左边吊着一个白色的袋子,装的是什么我不清楚,她的表情很少,不怎么会笑,说话的语气也一直都是平的,远远看过去,她像一个漂亮的人偶。她穿着对襟白衬衫,呢子碎花短裙,想必是学校的女孩校服,她的头发没有绑上马尾,头发散落着,她的刘海很长,遮住眼睛的视线,她惧怕别人的视线吧。…………
我说:“你有什么心事吗?”
“………”她低着头沉默着。
“你那天说的话让我很担心。”即便担心我也无能为力,想到这一点我心上就如同划开了一个口子。
她摇了摇头,欲言又止,然后卸下背着的书包,拿出速写本来,翻到了我看到她画过的那页,是那向日葵田。
“我想去看看。向日葵。”
她的父母是社会上流人士,对于孩子的旅游问题金钱不是问题,但带女儿去小岛看向日葵田是入不了他们的眼的,他们家的规矩与其说是严格,不如说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女儿的愿望什么的是不重要的,他们只会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这样他们开心了吗,我没有说这话的资格,但我内心呐喊着,我就是想说。
无论从任何角度,我都不可能带着这孩子去小岛看向日葵,我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劣质品,我连自己都无法拯救,更别提帮助别人,可是,总掂量着社会的秩序,我想我什么都做不来,迷茫着的我是否有指明他人道路的能力呢?我觉得我是没有的,正因如此,我比别人更清楚孤独的感受,寂寞的苦楚,我可以和他人寻找出口,这样想是不是有解决方法呢?
鸽子对我说:“事情只关于自己,想做和不想做都差不多。”那为什么不选择去做呢,纵然没有意义,纵然是徒劳的,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就关于我一人,它就有做的意义。
我说:“给我想一想。”
我出了门,在街道上没有目的地走着,我把我二十二年来的人生从头到尾地快速浏览了一遍,从幼儿园的黄色的帽子,到住院的白色的窗帘点缀的玻璃窗户,最后到大学联谊的金黄的啤酒花,我将记忆的抽屉翻了一个遍,我在寻找着经验和方法,但我没有能找到一点有用的信息,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欲望,不期待加薪,不等待下个月的杂志和新的漫画,过得行尸走肉,往往这时候人大概死了,社会上有着那么多让人失去信心的东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唯独活着确实闪闪发亮的事,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
我知道这样的道理。
我能为这个孩子做什么呢?
带这个孩子去看向日葵田吧。
我抬头看漆黑的天空,隐约有星星在闪烁,我转身回去。
“我带你去,什么时候?”
“明天早上,在车站,大哥哥你有帐篷吗?”
“你要在那里过夜吗?”
“我想看漫天的星星。”
“你真是任性,帐篷可以去借,但只能住一夜,你的父母会担心的。”
“他们不会的,他们不是家人。”
说句实话,我不知道这孩子经历了什么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无论怎么说,说自己的父母不是家人的这种话,我发自内心地觉得很恶心。
“说父母不是家人未免——”
“大哥哥,他们不会担心的,他们虽然是我的父母,但他们不是我的家人。”
我没有任何话应对她,她是我人生里最大的变数,她这个美丽的娃娃里面装着什么才是我所担忧的,她的双瞳里映照出什么样的世界,一定是个扭曲的世界吧,我不是她,但我能对此确信。
每个人遇到的事都是差不多的,只是遇到的时间是不同的,但她对于这种想法是最有力的驳斥,她遇到的东西是特殊的,遇到的时间也是特别的,她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时间稍微晚点,我早上去租帐篷,下午在车站见面好么,不,就在我家楼下,我怕你走丢。”
“好的,我知道了。”
在她的世界里,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危险什么的她都留意。
“我知道了,我送你回家吧,别和父母说你来过我这里,我会被警察审讯的。”
“你放心吧,大哥哥。”
我带她走出了民居,她长着小孩的脸,但不像一个孩子,上帝对这个孩子太残忍了吧,我不由地感慨。
一瞬间,路灯点亮了,成两排延伸到远处,像飞机起跑灯一样,我们走下坡道,为了安全我紧紧地抓住女孩的手,对面走来两个妇女,看我的样子觉得是哥哥和妹妹,看了几眼就走过去。
女孩的手像玻璃纤维制品,好像一用力就会掐断一样,我好像握着一个沉重粗糙的石头,这是我对她的情感。
我一定带她去看向日葵田和星空。
我暗自下了这个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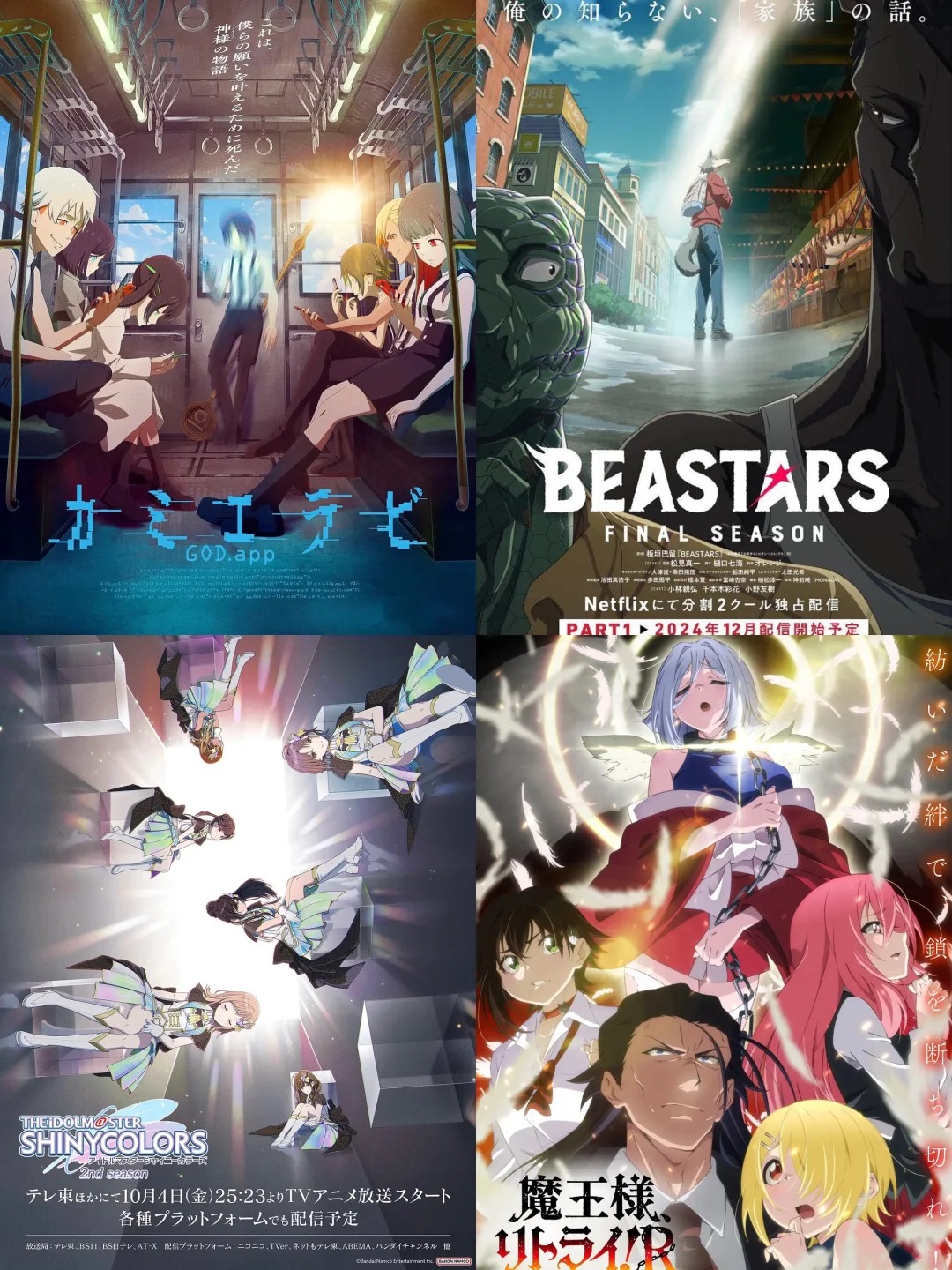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